与友人王六同去南阳,他说,到南阳,不能不会会南阳的“曲友”。由此,我便跟随着他一起走近了大调曲子——这种被称为“活化石”的一种民间文化;由此,我才知道因为共同的对大调曲子的热爱,演唱、演奏者还有“曲友”这个称呼;由此,我与他一起见到了他的曲友。! ~% m% z4 Q' r$ R
王六是周口文艺圈里的一个“怪才”,因为他既擅长弹三弦,又擅长抓筝,所以成为曲友中的一员——为唱曲者伴奏。在王六的一位已经二十多年未见的曲友家里,简单的几句问候之后,他们唯一的话题就是大调曲子,他们在感叹过谁谁谁没有了,问过谁谁谁是不是还健在之后,又感叹着没有年轻人愿意学这光调六就有二三百个的难听难学难唱的“老古董”了,现在就剩下几个老头没有听众、自玩自唱地瞎哼哼了。从他们的感叹中,从他们的痴爱与执著中,我感觉得到:到了应该珍爱、应该保护这种古老的文化的时候了。+ Q7 a, J5 X/ n' s1 j
说着说着,王六手执身边的一把三弦开始拨弄,几声过后,他的曲友手托檀板,向在座的恭敬一番,轻轻击板表示“献丑“,然后正襟危坐,闭目而唱:“久闻大名未曾相逢,今日相见果然英雄;千里迢迢来会宾朋……”声音一发出,房间里就弥漫着一种历经二十年依然存在的一种熟识一种默契一种友谊。南阳的音,周口的调,在此融为一体。怪不得他们说:“天南地北唱大调曲子的人凑在一起,最先说的不是吃饭,不问住哪儿,而是先唱上一段。”
没有宽敞的场地,只有一间阴暗潮湿有小屋;没有如潮的观众,只有我们两个同行者外行的叫好。也许,这些对他们而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向这个世界倾诉。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倾诉,当官的用权力倾诉,富有者用金钱倾诉,画家用恣意的泼墨倾诉,作家用手中的笔倾诉,家庭妇女用唠叨倾诉……而他们,在用大调、用琴弦、用声音抒发着自己的情感。
在他们陶醉曲中的时候,我也不由得思绪飞扬。说实话,我不懂大调曲子,这样近距离地接触、感知,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接触它,纯属偶然。/ }' @4 K% n- n8 T& A* a( Z3 u
当时走进周口市临近关帝庙的一条僻静的小胡同,实属偶然。在一个破旧的透着昏暗灯光的小屋前,围满了人,走近,才听到有人在唱着什么,还有古筝、三弦、二胡、檀板的伴奏。走进屋子里,在一个横条板凳上坐下,才发现六七人就将这小小的屋里挤得满满的。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子正卖力地唱着,听了半天才听清其中唱到“梁山伯”,想是化蝶的故事。他方唱罢,一人站起又接着唱起来,通过其中偶能听懂的字眼,知道唱的是罗成。段子很长,在听不清唱词,感到无聊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用目光研究几个伴奏者:拉二胡的老人胖胖的,一直卖力地拉着,眼皮一直没有抬起,让人觉得他一直陶醉在曲子的世界里;弹三弦的随着演唱者时快时慢的节奏不时地变换着手法;弹古筝的时而轻轻滑过琴弦,时而铿锵有力……说实话,无论是看眼前的这五六个中老年男子,还是听他们浑厚的声音,都没觉得好听,甚至觉得有些难听,有些土气。演唱者嗓子有些哑,端起水杯啜了几口。我看到放古筝的破桌上摆了三个搪瓷缸子,每个杯口都掉了不少瓷,让人感觉这杯子与大调曲子一样悠久、土气。据说,原来在周口有七八十个人可以演唱大调曲子,但现在也只余十来人了,而且年纪都偏大。" g1 P- v) n4 J# Q; Z U
这次来到南阳,再次接触大调曲子,仔细地品味,才知道自己第一次感觉“难听”,是对大调曲子的误识;觉得它土气,更是一种门外之见。请教他们才知,大调曲子是“文雅之乐”,唱腔高雅,乐曲艰深难学,早期多为官宦豪门消遣逸乐之用。唱曲者演唱时多闭目,就是缘于对内眷的回避与尊重。解放后,大调曲子才由厅堂走上舞台,走入农村厂矿。
此时,王六的老友在唱《潇湘夜雨》,让我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位五十多岁,看起来土里土气的男人,竟将林黛玉的多愁、善感、伤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样让我想不到的是,唱词也很有文化内涵:“沥沥细雨伴清风,触动闺阁儿女情。林黛玉闷坐香闺独对孤灯,思想起终身大事长叹一声:外祖母怜悯于我,才流落在贾氏府中。人见我锦衣玉食,难解我满怀苦衷。林黛玉衔首致意倚靠窗棂,思想起终身无依无凭,怕只怕飞雪落花染泥泞……”
他们弹着、唱着,我听着、想着,不知不觉已是十二点多了。来到一个小饭店,由饭菜的味道自然而然地想到大调曲子的味道,王六说:“现代的可以锐意改革,但传统的还是应该有些传统的味道,这就像战国时的青铜器,你拿出来给它刷刷漆,再整治整治,它就不是那个味道了。”他的话,赢得不少赞叹。从他们的对话中,我知道大调曲子的取材十分广泛,有历史故事“三国”、“水浒”,有古典名著“红楼”、“西厢”以及民间传说“白蛇”、“梁祝”等,也有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如《安安送米》、《李豁子离婚》……
吃过饭,已是中午两点多钟,听说南阳镇平也有几个曲友与南阳市的一帮曲友正聚,其中知名者黄天赐也在,我们一行人便赶了过去。刚走到楼梯口,就听到从一个房间里传出弦乐之声。一曲终了时,我们走进房间。相见的客套自然是以“大调曲子”为主题,五六说我们主要是来学习,黄天赐说是相互学习。王六说,这可不敢当,就像捞鱼,周口的几个玩家是“漏网的”,南阳可是基地呀!我想,这种说法不仅仅是谦虚,还因为大调曲子是南阳地区的主要曲种。但即使这样,我依然看到了它的“曲高和寡”,房间里除了我这个外行是个纯粹的听众,其余几人都既是听者,又是唱者、奏者。无论是演唱还是伴奏,都看得出他们的自我陶醉。! w0 T" x5 M. c( J. }) k/ w+ R7 |5 Z5 U
窗外,雷声滚滚,雨落声声;屋内,檀板在敲,曲子在唱,余音在绕,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文化在充满现代文明气息的房间里弥漫……! u/ @0 c' x0 e) L( }
也许因为我没有那份陶醉,我想到了大调曲子越来越少、越来越老的玩者与听者,我想到如果再不及时地拯救,它即将成为过去;如果不及时地保护、传承,它会在我们的记忆中消失。我想到了那一句:“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2005年7月)( & ~' _& } i; 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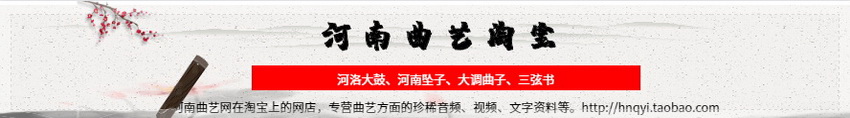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