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一年春节,大年初三从老家开车带妻女回洛阳后,便接着投入年前修改的长篇小说《凤凰鸟》中。今年的天气奇好,雨雪皆无,风也平和,就想起逛洛阳庙会。洛阳庙会从大年初一开始直到初六结束,地点在隋唐植物园。从一些报道中知道,庙会有许多洛阳的民间传统节目,比如木偶戏,比如河洛大鼓等等。别的且不论,河洛大鼓得去听听,于是约请同乡画家,也是老同学董修群前往,觉得二人还不够热闹,又约请二人的共同同学任汉稳一同去,由我开车。
我们到隋唐植物园门前不禁吓了一跳,用“比肩接踵”、“人山人海”这些词不足以形容其人多。买票进得园内,条条大道就像河床,而人则是河水,平静而缓缓地流动。我们在那里玩了半天,果然看到的内容丰富,看到了木偶戏,听到了河洛大鼓书。河洛大鼓书的摊前人不多,场面也不大,先是一个孩子说,后来一个老人说,一听,我熟悉此人,这人就是说《刘秀喝麦仁》那个人,我买过他的磁带,如今人已老,嗓子不行,口齿不清,说的内容也老,有一些失望。
看了洛阳庙会后,一连几日在家中静下心来修改小说,偶然和楼下邻居说起话,宝丰正月十三的马街书会很热闹,兴趣徒然大发,想去宝丰马街听书赶会。好多年了,抽不出时间。在网上搜马街书会的消息,名气大得很,它是宝丰的一块金字招牌。越有名气,越发吸引人,年轻时到处流浪的那种情愫又活在心里。心想找个人作伴,比较符合现在的身份,打电话给修群先生,画家忙得很,正在赶一幅据说能超过《蒙娜丽莎的微笑》的画,这便罢了,不能因为我而使世界艺术受损失,因此就决定一个人出行。
打点了简单的行装。正月十二那天下午三点,从洛阳坐上火车,两个小时便到达平顶山西。此地是一个小站,因是春节,街上人挺少的。车站出口路边有一些饭店生意。我步行往街中心走,只见房舍零乱,路也很窄,而且很脏。打听方知,此地虽叫平顶山西,其实就是宝丰,距离平顶山市尚远,还有二百来地。这里是个镇子,名子叫杨桩镇,一个十字街,三轮车夹在公交车中跑得飞快,此地距宝丰县城很近。
街上很多商店没有开门,几个饭铺却是食客迎门,他们背着包。一看便知是外地人,再一搭话,知道也是来赶马街书会的。
先找地方住下,问了几家,都是客满,最后问到十字街附近一家,人家尚有一间没有售出,我交了三十元住下了。进屋才发现,很差,是门房改过来的,不隔音。但屋子倒是挺大,一个电视更大,也算干净。古人说,好住只一宿,出门在外讲不得个满意不满意,这比起当年流浪伏牛山住店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了,那时没有现在有钱,但那时很年轻。
安排好住处,就到处走走。这宝丰县,在我心里是很有份量的,虽然是第一次来。在我心目中,宝丰的有名不在酒,而在人,我说人,指的是赫赫有名的白朗。
民国初年,白朗在宝丰揭竿而起,反对袁世凯,袁世凯派兵弹压很久,没有成效。白朗的人太多了,有十几万,从宝丰向东攻入安徽,向西进入伏牛山,直打到甘肃一些,队伍盛时,势如破竹。据查历史,白朗这个人很仗义,起兵后,孙中山派人来帮助他,也是想掌握他,要他转向革命。可惜孙中山派来的人没能力,使白朗队伍成了一个到处流蹿的乱军。因而史学界,有的称他为土匪,有的称他为起义军。
白朗闹腾了几年,终被镇嵩军所灭。宝丰的大刀客英雄梦也做完了,但他的英名却留了下来。小时候,我就听大人讲“白狼娃”和“黑狗屎”的故事,说是白朗和黑狗屎是患难兄弟,二人很有些武艺,有一天二人晚上住店,白朗是腿勾着房梁睡觉的,而“黑狗屎”却是贴在墙上睡着的。至今我不明白,讲故事的人为何把“黑狗屎”说得那么厉害。
即使称白郞为土匪刀客,也算得上一个不小的英雄。因而我对他很敬仰,我曾搜集了他的许多资料,最早的是《河南文史资料》第一辑,里边有篇不短的文章,叫做《白郞起义始末》,是现在的河南大学、当年的开封师院师生调查后写的,很详细。并想以此为材料写一部小说,后来上网找资料,便打消写作的念头,因为白朗起义这件事,早有人写过小说了,并且还不止一个。但我还是没有完全放弃白朗,在长篇小说《伊河秋声》里,有章节是有关白朗的事,但不幸的是,写得过于粗糙。至于宝丰这个地名,我最早在小说《火烧红椿寺》里写过,那是因为牛金星曾是宝丰人,就塑造了一个宝丰人、半吊子秀才、木扎岭山大王杜平宽,对这个形象,我是有点满意的。
话拐弯了,还得拐回去,正月十二那个傍晚,在杨庄镇转了转,对宝丰印象改变了不少,想象中的宝丰县应该是山,但这里是平原,平得还一望无际。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听说宝丰县城在二里外的地方,就搭三轮车去了,站在城边的大转盘地方,看见的是高楼林立的城市,拍了几张照,觉得没有什么新意。正感觉没什么意思,没想到马街距县城也就十里地,有公交车往马街去,没想多少,就搭街到马街去了。沿途全是麦地,公路也不宽,又挺破的。
但是坏了,到了马街村边,天已擦黑,问了一下,人说马街距此还有二里地,本想步行去,又觉得生地方,就又搭三轮车,花费五元钱,人家把我送到村里。
所谓马街村,村子很大,但街道很窄,而且弯曲,都是农村的街坊,和我相像的马街相差很远。本想晚上这里有会,有说书唱戏的,和自己小时候在农村一样,晚上到处跑着看戏,好多年不在农村生活,农村的景况已经生了,但我也太弱智了,高估了人们的热情,马街到处黑乎乎的,没有会,没戏,没有说书。
后悔了自己的冲动,明天就要来的嘛,何必天黑了还要跑一趟,最要命的是没有公共汽车了。
我没有其它想法了,就是回去,回到杨庄镇我定好的旅馆去,要打一趟车,我还没有那种气派,就习惯地寄希望于自己的两条腿,往回走吧。
我挎着我的小挎包,并不慌张。天全黑下来,但我认得路,我顺着公路原路回去,沿途有过往的车辆,刺眼的灯在黑暗的田野里显得格外明亮。
寒风从田野里掠过,扑打在脸上,但我身上却得热乎地。我边走边想,当年红军战士离开他们的热土,行军到长征途中,一个掉队战士,会想些什么呢?又想起我看过的许多小说,一个男主人公阔别家乡回来,天黑到了家中,“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那是何等的温暖,“风雪”二字叫人怦然心动啊,那个回家的情景叫人有无尽的遐思,让人说多幸福就有多幸福。
于是我想起我的父亲,父亲是一个教师,我小时候,他在县城一带教书,每逢星期天都要回家一趟,或者月儿四十才能回家一趟,我记得,有无数次,父亲用一根棍子挑着他的一个旅行包,在夜很深时喊门,我们给他开了门,那时我心里感到非常的幸福。并且有几回,父亲还给我带回吃的、小人书、手枪等东西。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有一回父亲给我带回了连环画书《白求恩大夫》,不仅我把书翻熟翻烂了,而且全村的孩子也借去看过。
我一个人缓缓地走着,月儿渐渐升高了,田野里由黑暗变成了白茫茫一片,正月十二的月儿,是一轮半月,但非常皎洁,《月是故乡明》,但这是他乡月,月色茫茫,月下行走着一个不很“断肠”的异乡人,也没有骑着瞎马,“夜半临深池”。倒是这朗润的月,使我有说不出的感觉,我为什么会一个人来到这里,我怎么不安安生生地呆在家里,陪着妻子女儿,安静地修改自己的小说呢?我想起了在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放暑假,自己不回家,而是挎着一个书包,逃票扒火车到连云港玩,第一次看到大海,心悸。那也是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我在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躺下,海边的蚊子那么大,那么欺生,咬得我直到天亮也没睡成什么样。
我又想起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洛阳矿山厂职业高中工作,放了暑假,我一个人背着包,包里有一个茶缸,一条毛巾,一把伞,从洛阳到洛宁,翻越老界岭。那是山生黑云的高山,说云即雨,但我沿着山上淘金人走过的小路,冒着迷路、被毒蛇和猛兽袭击的危险,翻过了老界岭,到了家乡县大章乡三人场村,晚上住在一户性薛的人家房外的柴棚上。那晚脚疼得钻心,不敢乱动。那夜也有月光,是新月,月光很淡,不久月儿便没了,天地一通漆黑,夏虫唧唧叫了半夜。隔河对岸是另一个村庄,能隐隐听见说鼓书的声音,敲鼓拉弦,说唱声历历可听,直听到我似睡非睡,后来真正到了梦中。
那是我独自外出旅行最难过的一晚,第二天醒来,一身的露水,我的脚仍然疼的厉害,几乎不敢下地,就从那一次,我落下了风湿病,许多年来颇繁发作,给我带来了许多痛苦。
但是我忘不掉,大清早男主人给我端来了一碗鸡蛋茶,我喝完上路了,直走到二十多里外才有了饭店。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对我自己很埋怨,我竟然没有再去三人场村去感谢那位姓薛的,很不义啊。
行在从马街到杨庄的马路上,在月光下,我的遐思仍然没停,使我想起另一次独自上伏牛山旅行,那是一次旅行时间最长的独行,跑遍了伏牛山的山山水水,使我对伏牛山有深刻的了解,它总在我的心里,拉起笔写点什么的时候,总要不自觉地写到它。那次把嵩县、栾川、卢氏、淅川、西峡、内乡、南召转了一遍,知道了伏牛山的性格。后来又专门去了一趟嵩南车村镇的红椿寺,为此写了一部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我觉得写得还比较满意。
单独外出旅行,思想在无边的陌生地,可以无穷地膨胀,可以膨胀成整个宇宙。就这样想着,慢腾腾地走过田野、村庄,当月光和星光淹没在杨庄的灿烂的路灯下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多了。
所幸,杨庄十字街上的一家羊汤饸饹面馆还开着张,我又一次吃到疲劳饥饿后的美味,那面真好吃啊!
车只行到昨天坐的车行的一半,便不开了,因为满路全是人,车根本走不了。那路上的人缓缓地像河水一样向前涌动。下了车,随着人流涌向马街,约莫走了五六里,才走进村子。沿途看见成队的警察,他们就站在路边,许多车辆就停在麦田里。
今天是大年十三,是马街书会的正会日子,我好不容易过了一道道气袋支撑起来的广告拱门,才移向主会场。通过一个石牌坊,上边写着“马街书会”四字。牌坊正门石柱上写有两幅对联:
其一曰:拜师学艺赶书海,寻根问祖踏歌来。
其二曰:一日能看千场戏,三天可读万卷书。
石牌坊背面:
把天作幕唱完天南地北大奇观,
以地为台道尽古今中外千年事。
过了石牌坊,发现路边各立一个高大的石壁,石壁一面刻着马季、刘兰芳等各人的手书题词。另一面记载着马街书会的历史。
我在石壁前徘徊良久,照了几张相,又请人给我照了一张有石牌坊的相,左看右看不忍离去。心想,什么是文化?这就是文化啊!石壁上记载,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艺术胜地,历史悠久。史载,书会最早起源于元朝延年间(公元1316年前后),到现在已有七百年历史。那时候,马街有个说书艺人叫马德平,一生德艺双馨,带出了很多说书的徒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这些徒弟出师独自去谋生,但在马德平每年正月十三生日这天,弟子们相约来到马街为马德平说书祝寿,久而久之,成了习惯,这马街便有了正月十三的书会。据人说改革开放之前,书会是在村里街上举行的,因人太多,政府把会址迁在应河岸边的田地里,并刻碑勒石来纪念。
政府扶持的事迹,大都发扬光大起来,马街书会在改革开放之初是最盛的时候。那时候,中国没有电视,甚至连电也没有,人们的娱乐形式很单调,因而说书很盛行,每县还有曲艺团什么的,宝丰县出了能人,看到了马街书会的巨大前景,就不断使它丰满起来,比如把会从街上搬到大田地里,政府同意,人们踩了的麦田,政府出钱把踩踏田全年的收入赔偿出来。
马街书会出名了,来此表演的早超越说书一个项目,像今年,相声、数来宝、山东快书、河南坠子、天津大鼓、苏州平弹、东北二人转应有尽有。
像今年的情况,麦田里搭了四个台子,分别是省、县各地的演出舞台。各台的节目都很不错。再者整个广场,到处都是说书人,有已经掉了牙,说话跑风的老者,打着简板说唱者,有七八岁的曲艺学校的学生,男女老少,有几个人临时搭火的,有夫妻二人一拉一唱的。到处都说书人,到处都是胡琴音。
但更多的是做广告宣传的,有唱戏耍猴玩杂技的,有套圈、算卦、卖旧书的。我买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文史资料《樊钟秀与建国豫军》,觉得买得很值。另有小商小贩,卖吃卖喝,都在大田地里扎摊。人们到处跑,到处看,到处听,照相的人特别多。
在马街书会上,美中不足的是现代的广告,他们搞得很花哨,喇叭特别吵人,把那些只有一个扬声器的小说书的声音全压下去了。若在场外的高地看会场,真是眼花撩乱,诸色人等,应有尽有,连医院的医生也来这里支摊坐诊。
我在书会上相中了几摊说书人,年岁不大,说的故事也较新,围着的观众也特多。其中说书的有两个瞎子,小瞎子有十几岁,在说书,老的有四十多岁,只顾投入地拉着弦子,孩子的声音清脆,说得极动听,给他们照了好几张照片。
田地有大型娱乐玩具,其中有一个大圆盘,能高速转圈,许多孩子坐,许多大人也坐。
杭州娃哈哈集团派员做广告,用美女俊男跳舞,很吸引眼球。
下午四五点多,许多人收拾家伙散会了,但麦田里有好多人围着几摊书摊听书,说书人说得很疯狂,赢得阵阵掌声。后来不知从哪里来了许多卖竹蔑做的飞鸟的人,不久飞鸟满天飞,很好玩,五元钱一个,我买了一个给孩子带回家。
临走,才发现,我已被弄得浑身是土,是在大田地里走得太久的缘故,这回可真正体会到土生土长以及“乡土”的味道了。
中午在会上吃了一碗饸饹面,做得很好吃,只是份量少了些。
马街书会散的状况挺悲壮的,曲终人散,至少我觉得依依不舍。其实昨天已经起会,已经热闹了一天,今天只是人更多,达到高潮罢了。高潮过后,便是平常,人们从路上,从麦田里散去,走得还怪急切,没多久,主会场人去大半,厚厚灰尘的会场裸露了出来。
这使我想起小时候在书场听说书,说书人把书说到高潮处,便忽然“这本书还通长哩,三言两语道不尽,同志们,请了吧,请了吧,待到明晚再接着说。”通常,乡民们哪里便就走了,议论一番,要说书人再往下续续,甚至这样几次三番,说书人把说书的家伙装起来,但还是重新拿出来往下再说一段。现在,在马街书会上,还有几家被围着的说书摊,大多数人四散而去,散去的场面怎么想着像打了败仗的电影场场面,败兵们在硝烟中交械,举着手垂着头慢吞吞地散去。
我也该走了,再晚,怕车不好坐。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在书场附近转悠,想看看哪里有卖说书碟子的,寻了半天,没有见到。说起说书碟子,这几年收集了不少。十几年前买了不少磁带,有王小岳的《老包访太康》,牛共禄的《困婵玉》、《姬高剃头》、《战吕布》,段界平的《刘秀喝麦红》,就是今年在隋唐植物园说书的那个人。这些磁带中,王小岳说的最好,他是栾川人,获过全国曲艺大奖,并多次赴台演出,可惜四十二岁那年突发心脏病去世,许多人写文章叹惜曲艺界陨落了一颗巨星。后来有了碟子,先后买了不少,有偃师唱家李新芳的《王金斗借粮》,《大脚姑娘花园赠金》,有孟津唱家张建波的《徐延召回京》、《朱麦臣休妻》。李春红的《罗成算卦》、《拳打镇关西》,胡中华的《傻子认亲》,胡银花的《白银娥救夫》,尚继业的《小三分家》。他们书说得各有千秋,我比较喜欢李新芬的《王金斗借粮》。这些艺人,我曾和李新芬、张建波说过话,那是三年前的事。
三年前九月份,洛阳有个非物质文化艺术节,河洛大鼓演唱点设在偃师。有一晚,我从洛阳坐车到偃师,晚上听了李新芬和张建波的演唱,近距离接触,两位艺人登台献艺,丰采照人,比起看他们的碟子感觉要好。那一次也是我一个人去,听罢说书,夜已深沉,我只好搭火车回洛阳,那车票真是便宜,是一元七角钱。
我之所以钟情于说书,完全是缘于小时候听书入了迷。小时候听《上海捉特务》,很长时间沉迷其中,一个人时总要哼着唱,唱得很痴迷。那时听说书,四村八乡跑着去听,因为一部书太长,一个村子说不完,就挨着村子听,说书人说书,由生产队派饭,晚上听书,白天工间休息时议论,中午还要听一阵,现在想想,农村生活那么纯朴、单调,仅一个说书的就把几个村子扰热闹了。
但是,如此繁荣的说书节目,随着中国人有电视,彻底把它冲淡了。后来干脆消失了,好多年没见到过说书人。只是近些年,人们要抢救和保护这种艺术形式,才又把它重视起来,老艺人几乎说不动书了,好多人已经作古,后继无人,年轻人又不愿干这行。说书过去传统的方式是师带徒,或父传子,带家族性质,但现在年轻人谁也不愿意学了。有了电视,有了电视剧,整个社会改变了,艺术形式也改变了。现在又有了电脑,说书这种形式只有上了网,人们或许还能看得到,但总之人气很差,年轻人干脆都不喜欢了。
其实用不着叹息什么,一种艺术形式的兴衰,完全是很正常的事情,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这才符合马克思哲学,符合辩证法。
但毕竟它光辉过,留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它像陈年佳酿,一旦遇到真正的饮者,那才是相匹配的佳话。我不担心它会消亡,它一直还像过去那样鲜活,在我的心中成长,以至于在去年写的长篇小说《伊河秋声》里,把说书写成了单独的一个线索,这条线索演绎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我曾为自己塑造的人物的命运而感动得流下泪来。
赶马街书会,回杨庄镇是步行回去了,没有车能开得动,人太多了。到了车站买了车票,还有一段时间,就照了几张车站的照片。天公凑趣得很,居然下了一场小雪,平添了几分浪漫。直到上了火车,天还飘着雪花,把地下白了。火车里人很少,暖气很足,车速也很快,带着我愉悦的心情回到了家。
偶尔又想起马街书会,总觉得有一种感觉心里知道,就是说不出来,时间久了,才明白自己的感觉到底是什么了。马街书会是土生土长的曲艺盛会,覆盖地域那么广,在全国那么有名,但说到底仍然是一个农村的集会,没有比较好的秩序,随聚随散,艺人们也很随意,演唱自由。至于集市的买卖,那更是具有农村的特点,不多赘述。和洛阳隋唐植物园的庙会相比,洛阳的庙会则太豪华了,秩序好,地方好,举行了那么多天,到处都很干净。我体会到城乡大型集会的不同特点,农村就是农村,城市就是城市。不过,有一点是相通的,所有去赶会的人,都有凑热闹的心情,这又使我感叹,和集会比较起来,宁静、独处,那才是出离境界的所在。
2011.4.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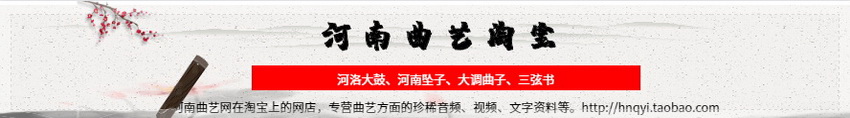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