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坠子是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地方戏,唱腔简单平直、宽厚粗犷,伴乐单调质朴、低沉悲壮,是最普通不过的民间说唱艺术,谈不上高雅,可称之为俗。已进入不惑之年的我,却特喜欢听,有时还随着喊上两句。去年春节,放假在家。我在网上搜索了好一大阵子,才找到了民间艺人郭永章演唱的《报母恩》,竟反复听了数遍仍不甘罢休。已上大一的女儿见我听坠子时手脚乱动,头也叩叩点点,两眼里还充满泪花。便说,傻爸傻听,专听傻腔傻调。
我不会责怪女儿对我的椰榆,一个从小在现代化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无法理解从那个偏僻贫困走出来的乡下人对坠子的偏爱。
记得小时候的一个冬天,村里来了个唱坠子的盲人。深冬的夜里,一盏带罩的煤油灯高高地挂在村口的一个大槐树下,风并不大,那破灯却一晃一闪的,总像是要灭的样子。盲人坐在灯下的一个凳子上,脚前的地上插着个特制的梆子,用绳系于脚上,脚动绳拉梆子响,清脆悦耳。盲人手中的那个高杆的弦子不但能奏出很好听的曲子,还能学鸡鸣狗叫、敲锣打鼓。盲人拉弦的动作很带劲,摆头摇膀,拧腰磨屁股,那时的我,对盲人的弦子很感兴趣,边听戏边用心观看盲人拉弦,所以最担心那灯会被风吹灭。
盲人唱戏是为了糊口,到了第二天,孩子都会闹着去给盲人送饭。饭只有两种,粥和窝窝头,送窝窝头的少,送粥的多,我亲眼见那盲人一连喝了十一碗粥,那窝窝头一个个都放进了口袋里。我问他,你咋不吃窝窝。他笑着说,备战备荒为人民。
坠子成了我童年的快乐,无论下地割草,拾柴禾,放羊或是去五里以外学校的路上,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会哼着那快乐的坠子调。我的童年是在窝窝头蘸辣椒的日子中过来的,生活虽然很苦,由于坠子偶有的出现,现在想起来并不觉苦,那苦日子像坠子里的戏,又像是童话,是一件件童话里的故事。
为了有盲人那样一杆弦子,买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己造。刮木竿、凿筒瓢、糊鱼皮、剪马尾、滴黄香……弦子总算造出来了。一拉声特大,有些难听,不是盲人拉出的那味。
后来有一个小戏班来到我村,也是唱坠子的,两男一女,男的一高一矮,高的是唱戏的,矮 的是拉弦的,那女的是个姑娘,长得廷俊,不会唱大本戏,只会唱小段,大家都说她是个学徒。不同与盲人的是他们有个大汽灯,夜里把它挂在大槐树下,咝咝的响着,刺眼地明。记得那晚女的先唱了个小段《拉荆芭》,说的是有一个叫严义的不孝之人,听媳妇话,将八十岁老母用荆芭拖拉到没有人烟的深山里,想把她饿死。十三岁的儿子严军知道后,哭着喊着将奶奶从深山找回。那女的连唱带哭,那唱是哭,那哭也是唱,只唱得男人两眼通红,女人挤眼抹泪,家后的柱子的奶奶竟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哭出了声,引得看她的人比看戏的都多。那高个子男人唱的是大本戏《小八义》,夹说带唱,似唱似说,节奏明快,吐字清晰,嗓音宽厚,唱腔圆润。那戏唱得个个人物活灵活现,那情节此起彼落,扣人心弦。村里的人们送他个外号叫“老少迷”。小个子拉弦拉得那真叫好,除了会拉曲子和学鸡鸣狗叫、敲锣打鼓外,还会学小孩说话。当时我除了戏迷,对那矮个子的弦子拉法也很着迷。他们夜间唱戏,白天睡懒觉,直到中午才起床。中午那矮子刚起来,我就找他要学两手,他说他懒得教。我把从队里枣红马尾上偷剪来的像个小鞭子似的马尾递给他。他很惊喜,就同意了,还给我的弦子又加了些黄香。他问我会唱什么歌,我说会唱《东方红》。他就教给我拉《东方红》。
从此,黄河岸边常常传出低沉的坠胡曲,和一个少年沙哑的唱腔。坠子,是我童年时的生活,少年时的歌。我喜欢坠子,喜欢坠子那低沉沙哑、宽厚粗犷、质朴自然的唱腔,也喜欢坠胡那淋漓酣畅、悠扬婉转、朴实明朗的演奏风格,如挟泥带沙的黄河之水,滚滚而来奔腾而去,悲壮宏大、如泣如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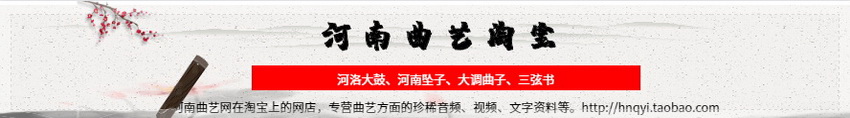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