邙山脚下,青要山尾,畛河西畔,华严寺侧,有一山沟,名平王沟,内有桃园村、楼下闩。门临溪水盘玉带,坐对南山翠若屏。这就是我的故乡,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
从记事起,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豫西农村,尤其是新安县大山以下的穷山村,不仅物质生活贫困,文化生活也相当匮乏。七十年代初,山区不通电,不通广播,直到上小学一年级,教我们的老师不知怎么搞到一台收音机,带天线,还缀两个一号干电池,声音小,噪音大,有时还得搁耳朵上听。就这样也是如获至宝,上课专门放给我们听,感到非常神奇。那时候白天大人们上工,学生们上课。晚上守着一盏小小的洋油灯(尽管解放后不叫“洋油”,改叫“煤油”了,但农村人还是习惯叫“洋油”),做完做业后无所事事,等待的就是漫漫长夜。
那时候,文化娱乐很少,没有现在都市丰富的“夜生活”,漫漫长夜如何消遣?偶而大队会演一场电影,我们就会跑个三四里路去看,当然也会跑到公社所在地仓头街去看电影,甚至为看一场电影跑个十里、二十里的路也是常有的事儿。请剧团唱戏对乡村来说,是非常奢侈的事儿,公社一年能唱个一两次戏,大队极少能唱得起戏,生产队想就别想了。想看场戏就得跑仓头、狂口、北冶、石井、竹园等地,打着灯笼,披星戴月,翻几十里山路,甚至打个通宵,戏台子下挤得胸口疼,仰得肚子酸,瞪着眼、张着嘴、掂着脚……受这一切罪,就为能看到一场戏。除了电影、戏,还有一项娱乐生活,就是看“耍把戏儿”,现在叫做杂技,或“马戏团”,也是我们小娃们儿的最爱。在粗糙的音乐里,铿锵的锣鼓中,翻跟斗、打侧脚、上老杆、耍气功、玩魔术很能吸引我们的眼球。每一摊儿“耍把戏儿”的都有一个专门的丑角儿叫“老菜包子”,故意显得笨手笨脚的,当众丢丑儿,出洋相,惹得人哄堂大笑。笑声荡漾在夜空,给贫瘠的乡村文化生活带来一丝活泼的生机。
电影、唱戏、玩把戏不是每天都有这样的“好日子”,平均下来一个月里有个三两天也是不错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夜晚,吃罢晚饭,大人们互相串门儿,坐一起拉家常,东南西北地扯,而我们小娃们打闹之余最爱听的就是大人们“说瞎话儿”。“说瞎话儿”是豫西农村的一种俗称。有的地方叫“讲古”、“说古”,书面上通俗地称为“讲故事”。“瞎话儿”按书面语言应该叫“民间故事”或“民间传说”。为啥叫“瞎话儿”呢?大概是因为这些故事都是民间流传的,口头讲述的,书本上没有写,历史上也没有记载,谁也考证不出来真伪,只能当瞎话儿听,这里的“瞎”就是假、不真实的意思。有这样一个“瞎话儿”广为流传:张三去李四家借东西,李四不在家,妻问借啥?张三说,借你家的“瞎话儿”本儿看看。李四妻回,他不在家。张三问,去干啥了?李四妻回,去打露水籽儿去啦!张三疑惑:露水有籽儿?李四妻反问:瞎话儿有本?这个故事就是谚语“露水没有籽儿,瞎话没有本儿”的来历。
“瞎话儿”虽瞎,但情节充满神奇、扑溯迷离,引人入胜。内容引古以鉴今,抑恶而扬善,多劝人诚信、守法、行善、尽孝等,趣味之余,给人教育与启迪。故“瞎话儿”老少皆宜,人人趋之。后来想想,仔细分析一下,“瞎话儿”也是一种说书,是最原始的说书。说书人好多书的内容来自于民间的“瞎话儿”。追溯说书的来源,早期唐宋时代不是称为“说话儿”吗?有文人把“说话儿”人说的故事记下来编成书,就有了“话本儿”。那时的“说话儿”和现在的“说瞎话儿”应该大同小异的,只不过那时就有“话本儿”了,看起来早期的 “瞎话儿”也是有本的,只不过我们农村大老土说的“瞎话儿”没有文化人来编写“本儿”罢了。当然这些都是现在才分析的,那时一个小屁孩儿是不会考虑这么多的。
听过最多的是我大哥讲的“瞎话儿”。大哥为人实诚,木讷,不善言辞,书读得不多,但肚子里装的“瞎话儿”不少,不知都是从哪听来的,总说总有,头头是道,让人佩服得不行。夏天树荫下,冬季炉火旁,我们陶醉在“瞎话儿”哩,听“瞎话儿”掉泪,替古人担忧。“瞎话儿”伴随着我们童年快乐的时光,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除了电影、唱戏、耍把戏、听“瞎话儿”之外,还有一项最重要、最普遍的文化娱乐活动就是——听说书!
说书,现在的理解应该是包括评书、鼓书、坠子及南方的弹词等曲艺,但那个时代到我们农村来的没有评书,更没有弹词。坠子书还是上中学时在寺上的前村闩听过一次,其余的都是大鼓书,就是现在所说的河洛大鼓。所以在我们这一带,说书就是河洛大鼓的专称。当然河洛大鼓也是后来起的名字,那时没有这个名称,都称为“说书”。
没上学以前,依稀记得就听过说书,也产生过许多疑问,明明又敲又打,又拉又唱的,为啥不叫唱书而叫说书?少时的印象里,有看书、读书、背书,书还能拿来说?别说那时懵懵怔怔,什么也不懂,就是现在也没研究透彻,“说”为啥不叫“唱”,“书”为啥不叫“故事”而偏叫“书”呢。别说咱文化低,捉摸不透,有些所谓的“砖家”、“学者”研究了一辈子,也得不出一些可以另人信服的说法。
农村人一年下来难得看几场戏、电影,但每年都至少可以享受几次听说书的“待遇”。比起唱戏、电影昂贵的花费来,说书要经济得多,也方便得多。人少,花费少,吃饭住宿都好招待。不用搭台,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点一盏油灯,烧一壶开水就可以开书了。所以说生产队演不起戏,看不起电影,但说书都能说得起。农闲时,说书人寻村串户找上门来,就连续说上几天,刮风下雨,干不成农活,聚到窑洞或其它避雨的地方美美的听上几天书,真是极好的一种艺术享受啊。
当然最另人振奋的还是我们这些半大屁孩儿,一见说书的进村了,马上就跟到后边簇拥着,欢呼着“说书的来啦——”。说书的往往有两三个人,进村后找个石桌或石凳坐下,有的孩子就跑着到队长家报信,有的主动给说书人当向导,领着去找队长,有的就围着说书人看稀罕,摸摸弦子,敲敲鼓,轰也轰不走。直到队长把说书的安排住,对我们大声喝斥:都爬回家去!给大人说说,晚上到学校窑听说书!我们这才高高兴兴地散去,单等晚上听说书。
乡村夏夜,凉风习习,夜幕降临,星火同辉。桃园学校门前的操场上早已人声鼎沸。说书人未到,听书的倒先聚集了不少。当然最积极的还要数我们这些半大娃们儿,兴奋得蹦呀,跳呀,嚷呀,闹呀,穿梭于人群之中,翘首以盼。一会儿队长把桌子拉开,凳子摆好,茶水备齐,说书的就到场了。掏出弦子,支上鼓架儿,钢板,鼓声就马上响起。开书以前,一般都是由徒弟先打起钢板,敲一阵书鼓。俗称“叫场”,即招徕听众,类似于戏曲开场前先打一通“家伙点儿”叫“急急风”,主要用于造势,告诉观众即将开戏了。随后钢板、鼓点儿配上弦子一通演奏,弦子拉得很热闹、欢快、紧凑,势如急风骤雨,听起来叫人紧张、兴奋。后来才知道开场前拉这一段弦子名叫“十八板”,是河洛大鼓音乐的前奏曲,能展现拉弦儿的功夫,技巧。往往一段拉下来,听众能拍几次手,喝几回彩。前奏曲过去,就该徒弟先“垫场”了。徒弟说的都是书帽或小段儿。徒弟嘛,肯定没有师傅说得好,人们都是这印象。对于徒弟说的书,大家都是爱听不爱听的。徒弟说书也就是借书场开头等待听众到齐的这个机会锻炼技艺的,反正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书场里很乱,有刚来的,有让座的,有大声打招呼的。小娃们听不进去书,也不懂顾面子,有的还高声嚷着:“换老师儿说!”,在一片喧闹中,垫场段儿就结束了,该老师上场了。
师傅上场就有师傅的派头,慢吞吞地归入正位坐下,不紧不慢地品一口热茶,拉弦的在这当儿吱吱呀呀地定弦儿,弦定好了,说家才清了清嗓子,敲两下鼓,就开口了:说书不说书,上场先背毛主席语录……
说书的背的毛主席语录都是当时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录,听到最多的就是:“要斗私批修。”“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阶级敌人斗,其乐无穷”等等。这都是适应当时形势的,以后再听到的就是“说书不说书,上场先做诗”了。
毛主席语录(或定场诗)念完之后,就是一番如“老少爷们稳坐两厢,听俺拙喉咙哑嗓,凉腔掉板,与您细陈……”之类的开场白,话没落点,就开始哼唱:“听俺慢……,咹——,与您——道——来——”。然后才不紧不慢,细条慢理地打起钢板,敲起鼓点,弦子也开始吱吱咛咛地拉起了过门,过门一完,就开始慢慢地唱了。
师傅说书大都如此,刚开始总是耷拉着眼皮,一副无精打采,少气无力地样子,开口说或唱都是缓慢、低沉的语调,给人一种慢吞吞,净松罢凉的感觉。如果你以为这说书人不认真,不搁劲儿,懒懒散散的,肯定不是好说书的。那你就错了,一方面说书人故意在开始时吊人胃口,另一方面说书人一唱一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甚至更多,是非常耗费嗓子和体力的,所以上场来养精蓄锐,强调稳,不能慌乱。说书的也说啦:前紧后松,到底不中,前松后紧,越说越稳。老婆纺花,慢慢上劲儿,大闺女游秋儿,越游越快。开始如果攥劲儿过火了,到以后热闹的地方反倒没劲儿了,唱不好了。只有松下来,才能紧上去,只有慢下来,才能快上去。所以说书人总是把精神头儿,把劲儿都攥在后边。初始时静似麋鹿,温如绵羊;进而似睡狮初醒,蓄势待发;高潮时如猛虎下山,排山倒海,势如破竹。
说书的大都如此,正说到紧要三关,五马岭上,热闹之处。比如眼看要打起来了,或闹得不可开交了,或刀架在脖子上生死一瞬间了……在这关键时刻就开始“撂挑子”,话锋一转:“眼看就是一场闹,打打钢板我要停。把书说到交关口,一言得罪众观众,要是瞌睡你就走,不瞌睡,喝口热茶接着听。”这一板书就算停下来了。
众人在说书人喝茶休息的当儿,也可以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拉拉家常,议论议论书情。小孩儿们出去尿一泡回来,还想着刚才说书人说的刀架脖子上咋办,是死是活?心里真痒痒,恨说书人早不歇,晚上歇,偏这个节骨眼儿喝什么茶,耽误事儿!就大声嚷着:少歇会儿,快开始吧!说书人笑笑,就拿起钢板,书鼓一声,书场皆静。
一晚上两板书、三板书就该收场了。刹书时老是撇了个想头儿,吊足了胃口,让人欲罢不能,明天不来听就睡不着觉。后来也逐渐明白,这就是说书人的“奸滑”之处,每次都是说到矛盾冲突,紧张热烈之处停止,给人造成悬念,吸引人听罢这场听那场,场次才能不间断地往下续,说书人的饭碗也才能持续地端下去。这就是“唱戏唱团圆,说书说零散”的道理。唱戏的是“拿不住奸贼不刹戏”,而说书的往往是越说越零散,你东我西,不能团圆。一旦团圆了,说书人也该“卷铺盖离庙”了。所以小时候我们听说书,听罢这场听那场,这村听撵那村,连续一个多月,却没有把一部书完整的听完过,最后也是心有不甘,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目送着说书人走出村口,消失在远处……
记事起记得来过好多摊儿,无数次的说书的。只管听书,也不会留心说书人是哪里的,姓什么、叫什么。依稀记得本县来的说书人最多,还有孟津、偃师的,上四年级时听过河北(这里仅指黄河北)过来的一摊说书的,印象中远没有河南的说书人说得好,说得带劲儿。老年人说东边有个段先儿说书说得特别好,那时很早的事儿了,可惜我们小孩儿们没有听过。我们只听过老杨先儿(杨德满,王管子的入门老师)、小杨先儿(杨保险,又名杨兆民),孟津李先儿(李玉山),五头郭先儿(郭黑蛋)的书。其它的就叫不出什么名堂了。但是来我们村说书次数最多,印象最深,妇幼皆知的说书人当数仓头大河口的王管子了。
王管子大名叫王长海,但人们记住最多的是他的小名,大名好少有人知道。只所以大家都熟悉王管子这个名字,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王管子来村里说书的次数太多了,从小出身跟老师杨先儿学徒时就经常来,出师后更是几乎年年不间断,可以说人们见证了他从徒弟娃儿到出师,以至成为“好说家儿”的全过程。二是王管子特别家常,平易近人,无论穷富,大人小孩儿都能说着话儿,每次来说书就象到家一样随便、亲热,而村人们也不拿他当外人,热情招待。大家时不时还开个玩笑,有人掂二话说,听王管子说书一股子王管子气。这话给王管子听到了,在书场公开地说,有人说我说书有一股王管子气,王管子气是啥气?好多人一时语塞,无法回答。就有小孩儿在下边高声回应,王管子气就是出离拐弯的气!童言无忌!顿时惹得哄堂大笑。王管子并不生气,也跟着大笑。一般人可能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但大家包括他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反倒觉得这种说笑更显得亲近、随和。三是人家说书确实有一把棕刷子,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试想如果他书说得不咋的,谁还会记着他,还会欢迎他?隔段时间不听王管子说书还想得慌,议论王管子怎么还不来说书呢?可见王管子在村人心目中的位置。
王管子长得相貌魁伟,中年发福后更显得人高马大的样子,个子高,身材胖,往书场一站,如半截铁塔一般,不开口说话,从气势上就已经镇住了场子。他又有一副好嗓子,嗓音非常宽厚、响亮,声如洪钟。夜深人静时,他的腔能听十几里。那个时代,说书从没有用过扩音机什么的,对他来说根本不需要。不管人再多,再乱,他往那一站,只一嗓子,书场立即静下来。有时候他在书场调侃说,我的嗓门儿大,大嫂们捂好娃们儿的耳朵儿,吓着了我可不管!你别说,有的孩子在下边乱窜,他吼一声,孩子们都不敢动了,乖乖地听书。
王管子说书很投入,声情并茂。说起姑娘媳妇来,扭扭捏捏,拿腔捏调,让听众忍俊不禁,笑得前仰后合。王管子善于说苦书,那天后晌,他说的是《拉荆芭》,说到苦处,声泪俱下,不住地用手绢擦泪,下边听众哭声一片,有几个老婆竟嚎啕大哭,书说不下去了,只得停下来,稳定一下情绪。王管子从书情里跳出来,笑着说:“看你们没出息那样,又没说着你们。”大家都又笑了,就是呀,这不是看闲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吗。就这样,一场书下来,哭哭笑笑。要不会说“唱戏的是疯子,听书的是傻子”呢?
王管子自幼失目,说书中人物动作、表情全凭自己惴摸。但他表演、比划起来却特别形象逼真。记得我都上小学二年级吧,那晚上他说的是《南京风云》,说到黑大个杀赵玉莲的情景,一手拿钢板做刀状,一手摸鼓做人头状,缩头咬牙,嘴里恶狠狠地一声“嘶啦”,提着血淋淋的头飞出去了。我们都把他虚拟的动作当成真的了,听得心惊肉跳,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听罢书,一个人得走一段夜路,吓得不敢回家了,脑子们老回旋着黑大个杀人的情景,怕黑大个冷不丁蹦出来,在半路哭了起来,一直等到家里人来接。
儿时的岁月,伴随着鼓声、书声和琴声悄然流失。曾几何时,土地包产到户,生产队没有了集体经济,说书人再上门时,队长推三阻四,不肯接待,我们听说书的次数也减少了。曾几何时,电视、网络、手机悄然闯入人们的生活,蚕食了说书的市场,使人们对听说书兴趣骤减。曾几可时,流行乐、泊来文化野蛮侵入,把说书一下子挤到了边沿化,成了时代的弃儿。从此我们再难听到几曾熟悉的乡音了。
后来我们小浪底移民搬迁,故乡成了万山湖的一部分,近几年因思念故乡、故去的亲人,每年七月十五都要回去上坟。曾经流淌着鼓声、书韵的故土,早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满目疮痍,触景感伤。早年曾经说书的场所,桃园学校窑依稀可辩,伫立良久,儿时的“说书”声仿佛又在耳畔响起,一阵秋风萧萧,琴声、鼓书渐行渐远,飘向了遥远的渺茫……
“说书”声正远离我们而去,却在记忆里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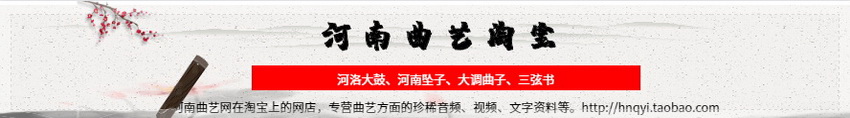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