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十八
有惊无险寺何山
入乡随乡,入俗问俗。有了头一天的教训,以后说书,第二板结束时再也不敢“轻言放弃”了。在舞台上说书,刚开始很不适应,觉得说书人与听书人好像隔点什么,但慢慢习惯也就算了,颇有居高临下的自豪感。在新安县说书时,因没有舞台,听书人把说书人围起来,几乎融为一体,扩音设备用处不大。但在舞台上说书,有了喇叭、话筒,音质效果就是不一样,不用攒着劲儿,伸着脖子,声嘶力竭地吆喝了,唱起来轻松自然,省力了不少。唱了几天,感觉离不开这玩艺儿了,以至王老师下定决心做出了置办扩音机喇叭的决定,此是后话。
诚如砖厂的新安老乡所说,灵宝人混熟不混生,这话一点也不假。两三天书说的,人便混熟了,人们再不会看见说书人,吓呼呼的,像躲瘟神一样。见面都要热情地打招呼,知道我们要洗个衣服什么的,忙不跌的提供洗脸盆、洗衣粉啥的,有些大嫂子们甚至捎带着帮我们洗了。因方言口语不同,有时也会爆一些笑料。
吃罢中午饭,没事儿,我领着两位老师在村里闲逛。因吃饭时间,大多数都是端着饭碗,见了面,少不得要打个招呼,问候一下。看见说书的来了,嘴边话就是:“吃啦没?”郭汉老师见问,忙不迭地回答:“吃了啦!”,有几个妇女听了捂着嘴哧哧地偷笑。原来灵宝话和新安县不同,吃饭不能说吃了啦,“吃了”和“吃料”谐音,吃草料之意,只有牲口才吃草料呢。所以灵宝人忌讳说“吃了啦”,常说的是“吃毕啦”或“吃过啦”、“吃啦”,总之不能带“了(料)”字。众人一笑,我和王老师也明白了怎么回事,笑着调侃郭汉:“她们笑你吃的是草料。”当着众妇女们的面,郭汉嘴咧了咧,眼翻了翻,没敢吭气,走远了几步,人家听不见了,才小声嘟囔着:“还笑话我吃料啦,总比你们吃逼强!”我们笑得直不起腰来。
王老师一边笑,一边大声说道:“汉儿,你不是统‘加是[①]’着哩?这一回吃‘加是’了吧?”
一句话出口,该轮到那一群妇女,包括几个中年人笑得吃到嘴里的饭差一点喷了出来。原来同是一句“加是”,在不同的两个地域,有截然不同的意思。王老师这句话里,用了两处新安方言的“加是”,头一个“加是”是“厉害、强势”的意思,多含贬意。如“你加是哩不轻!”第二个是 “吃亏,不沾光”的意思。而在灵宝话里,“加是”是一句“带把儿”的脏话,隐指男性生殖器。如新安县常说的带把儿脏话“去球吧”,用灵宝话说就是“去加是吧”。王老师上面这句话按新安县的方言来说,没一点病,意思是:“汉儿,你不是可厉害,可能着哩,这一回吃亏了吧?”翻译成灵宝话,味道就变以:“汉儿,你真像个球哩,这一回吃球了吧?”这样一翻译,难怪大家都笑得喷饭了。
说书稳下来了,为进一步广结人缘,提升人气,为说书服务,进而创收。二位老师不失时机地操起了第二职业——算卦。
郭汉老师算卦,从来不照书本,也很少批八字,善于“一口断”,张嘴就来,却能说得极准。看似信口开河,却又入木三分,句句戳到痛处,挠到痒处,让人瞠目结舌,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知用的是什么“旁门左道”,弄得真的好像有“耳报神”似的。这一点不但王新章老师自叹不如,连王管子老师也弄不懂他的徒弟有啥“外门儿”和诀窍。
正因为郭汉有“这把火儿”,到哪里都是风生水起。都说郭汉活动能力强,人缘好,善于交际,其实也没什么诀窍,就是凭借算卦能唬住人,人们都很乐意和他打交道。人家就有这点本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不超过三天,就能混得很熟。在灵宝亦然,头两天和我们在一起,三天以后,除晚上说书外,白天基本见不到人了,走东家串西家地给人算卦,忙得不亦乐乎。
别看郭汉体态短粗,个子不高,一脸络腮胡,其貌不扬,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却极有女人缘。他去别人家算卦并不是自己摸去的,都是人家管接管送。接的人如果是男的,老头或小伙的,往往扭扭捏捏,推托有这事儿、那事的不想去;接的如果是大闺女、小媳妇的,慌得比谁跑得都快。为此王老师一面笑骂郭汉“成色瞎,见妇女走不动。”,一边嫉妒人家有这本事,不服气不中。考虑到人家姑娘家给他领路,按着肩膀,拉着手啥的不合适,怕难为情,我提出把郭汉送去。谁知郭汉不领情,委婉地拒绝:“武成你歇着吧,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自己会去。”嘿,还嫌我碍手碍脚哩。不去就不去,谁想去当电灯泡?反倒落个清闲呢。
与郭汉老师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老师一身正气,一本正经。算命、批八字认真细致,每断一事都得有书可依,有据可凭,从不胡来。虽然算得也很准,找上门的络绎不绝,但很注意出门人避嫌,从不轻易到别人家去。实在抹不开了,也不让别人领路,好像别人会给他引到沟里似的。像黄香膏药一样沾住我,甩也甩不离。弄得他去哪,我得充当火车头,把他拉到哪。
人熟了,大多都被挽留在农家吃饭,很少去饭店了。灵宝的农家饭差不多顿顿馍、菜、汤,很少吃面条。做饭用的锅是固定在锅台上,轻易不能动的。大多烧柴火做饭,少见烧煤。上面蒸馍,下面烧汤,馍熟,汤也烧好,既省事,又省时,简单快捷。条件差的家庭吃蒸馍,喝蒸汤水,就咸菜,凑合着就是一顿饭;条件好的还会抄几样菜,或配几个凉菜。那个年代,尽管灵宝比较富裕,但主粮仍然不足,蒸的馍大多都是玉米面虚糕,条件好的掺一些白面,只有极少数富裕的家庭才能吃到纯白面馍。听说洛阳人习惯吃面条,人家中午时会破例,特意给我们做面条吃,但每人只有一碗,再回碗没有了。面条是淡的,桌子上放有盐和菜,咸淡自己调。就这我们已经是享受到外宾一般的高级待遇了,让人感激不尽哈。
短短的一个月,我们适应了灵宝的方方面面,从生活到行艺逐渐与当地接轨,进而完全融入。豫西边陲——灵宝终于张开了温暖的怀抱,宽厚地接纳了洛阳的河洛大鼓。
说书生意稳定了,闲下来就开始考虑技艺的事儿。
按王老师原来的说法,只要努力,说书弦子一年的功夫应该差不多了。自去年麦前学艺至今,不觉已快一年,还没有达到王老师所说的“差不多”水平。除初学时老师抄的几个常用过门基本熟练外,又学了几个新过门。指法、弓法等基本功自认为也比较扎实了。指法的揉、滑、打音逐渐娴熟,弓法的长弓、短弓、大弓、碎弓、顿弓、连弓等,以及抖弓、甩弓、捏弓等运弓技巧也有了较大的长进。唱腔中间的大部分小过门一般都能随机应变,或填空儿,或补缺,或转折,或承上启下,都能凑合着应付过去。弦子是为唱家服务的,侍候唱腔的包、烘、托、让等要领也有所领悟。
当然取得这些小小的成绩和进步,老师虽然看不见,但心知肚明。不止一次地说过:“武成的弦子现在中啦,好多东西都掌握住了,该进入实践阶段啦。瞅机会把你推到前面领头弦,俺们跟着你溜。”
我表面上仍然谦虚:“哪里,哪里,可不中,还差远哩。”假意推辞一番,“可不敢啊,我哪能领住主弦啊?”内心里却在想:其实早该让我试试领头弦啦,不让尝试,怎么知道中不中?可哪有尝试的机会?有两位老师在前面竖着,能轮到我吗?即使给机会,让领头弦,心也虚,胆也怯,也很难正常发挥啊。况且仅说说而已,压根也没有给机会啊。老缩在老师的翅膀骨儿下,放不开手脚,啥时候有个“领头弦之日”哈。除非,他们其中有一个病了,或有极为特殊的原因,不能上场领主弦了,到时候,没有指望,没有推托,岂不是下雨淋(轮)到当院,淋(轮)也淋(轮)到我啦?一切不是都顺理成章哈。
哈哈,这种念头只是在心里想想而已,打死也不敢说出来。为了想领头弦儿,竟然扒着老师害病或者出点事儿,想拉头弦儿想疯了?这徒弟是不想混了吧?老师要知道这种想法,可得摆个十大碗整桌叫我吃吃,祝贺他教了这么一个好徒弟!
想归想,睡到椿树下做春梦吧!但也有“好梦成真”的时候,还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还真地来啦。
在灵宝川里说书久了,腻了,很想上山转转。听说山区风景好,空气新,山里人更厚道,待人更朴实。老家新安县在山区说书的多,对大山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怀,说不出的亲近感。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平原说书,想着山里,总憧憬到山里说书更美好。想去山里并不难,咱有一张证明,如一柄利剑,可以“逢山开路”,所向披靡啊。于是,挥师东南,挺进寺河山。
寺河山位于崤山腹地,“山因果而发,果因山而名。”灵宝寺河山的苹果中外驰名。可惜我们来得不是季节,无缘品尝“亚洲第一高山果园”清脆多汁的苹果,只能看到漫山遍野的苹果树,抽着枝叶,黄白相间的花儿点缀其间,把整个寺河山妆扮得碧绿青翠,生机盎然。山里的空气就是好,登高望远,心旷神怡。但是山路崎岖,上坡下岭,让人腿疼腰酸,气喘吁吁,汗流满面。

山区的人们居住比较分散,没有平原地带人口集中。平原地带一村一大队,集中说几天就可以了。而山区一个大队管辖好几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一般都是一个生产小队。大队得照顾到每个生产队,每个自然村。最公平的办法就是分派到每个生产队演出一场,费用由大队统一结算,这样谁也不吃亏,谁也不沾光,免得闹意见。哪个队想多说(书)的话,费用自理。公平是公平,合理是合理了,但说书的得多跑腿了。这个队说(书)罢换那个队,村与村之间多则七八里,少则二三里,山路通车不便,况且那时候车很少。说书人只有开动11号车,玩地奔儿。
那天,我们从这个村起身到那个村,全程有六七里山路,需要下一个坡,过一条河,上一道岭,转一个弯儿,抹一个角儿,才能到一个藏在东山洼的小自然村。早饭后,问好路,精神抖擞地启程。下坡路好走,心情舒畅,虽称不上一路高歌,但郭汉老师嘴里一直没闲着,不住地哼唱着有点跑调的豫剧“西门外放罢了三声炮,伍云召我上了马鞍桥。”马鞍桥上没上去,小桥却来到了。一架用木棍搭成的简易小桥,横跨在本不太宽的小河上,驮着我们过了河,开始上坡了。
一道起起伏伏的土岭,一条曲曲弯弯的土路,路不算宽,也不算陡,蜿蜒着向上延伸。路两边缠绕着一层层梯田,间或夹杂着一行行果树,像系上了一条条的绿玉带,春意盎然。
虽称不上爬山,但至少是上坡。上坡路远没有下坡轻松自在,没走多远儿,早已累得气喘吁吁,郭汉老师的“话匣子”已经断音,伍云召不知跑哪去了。大家没心情说笑,也顾不得东瞅西望,只管埋头走路。
上坡路并没有一直向上,通到岭尖儿,而是至半山腰开始顺梯田绕岭环行。路渐渐变得平缓起来,走着不是那么费力了。郭汉用手抹了抹被汗水浸湿的络腮胡子,说:“慌哩是球!有多少鸭子愁着赶不到河里?紧趁庄稼,消停生意。武成,赶紧找个地方歇歇。”
歇就歇,谁有意见?四下看看,面前就是一块比较平缓的麦田,麦苗刚开始拔节,绿油油地煞是好看。还找啥哩,这就是个休息的好地方。于是就放下行李:“原地不动,休息。”
这是一块窄长状的梯田,顺岭势弯弯曲曲地向两端延伸,望不见头尾。路紧贴地里边的土壁,比麦田略高出一个台阶。路边儿新发起的草芽儿还无法覆盖去年遗留下来,早已干枯的密密麻麻的杂草,形成了一溜干草坪,像地毯般的柔软、舒适。
先服侍二位老师在路边的“地毯”上坐定,然后夹在他们中间一屁股墩在草坪上,松了一口气,可以放心地歇一会儿啦。不歇没事儿,一歇就歇出事来了。
搁往常,王老师性格刻板,不苟言笑,从不手狂、嘴狂,一派正义凛然的样子。郭汉生性“水嘴”,爱说笑,嘴贱,手贱。搁伙计之间,经常去王老师面前毛捣,做一些小动作,来一点恶作剧。王老师一般不跟他计较,也不还手,偶尔逼得急了,才说笑打闹一番。
合该出事儿。今天他俩好像角色倒置了。郭汉不耐热,好出汗,可能跑得累了,没心情说笑打闹,往地上一坐,动也不想动。倒是俺这位王老师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异常活跃、好动,站没站像,坐没坐样。坐那不大一会儿,好像屁股下有蒺藜一般的坐不住,悄悄地摸着站起来,不声不响地从我面前绕到郭汉面前,离不远处又摸着坐下,手闲不住似的在干草坪上乱摸,摸来摸去拽着了一根干汪汪狗草。汪汪狗草很普遍,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又叫“狗尾草”,因结的穗儿毛茸茸的酷像狗尾巴而得名。
王老师拿这一根汪汪狗穗儿做毛捣的武器,开始向郭汉发起了攻击。先是摸索着用毛茸茸的穗儿去触碰对方的手。郭汉感觉手痒酥酥的,还真以为是毛毛虫呢,就往我这边挪了挪。王老师并没有见好就收,反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起来,拿汪汪狗穗儿继续往对方脸上戳。郭汉觉得脸上毛茸茸地像爬了一条毛毛虫,不禁有些疑惑,这季节咋会有虫子呢?顺手一抹,碰到的东西不像是毛毛虫,听见王老师“噗嗤”一笑,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搁往常,这一戳就捅住了马蜂窝儿,郭汉也不是饶人的主儿,一定会奋起反击的。谁知这次人家非常地大度,能忍,只是笑了笑,坐着没动,大有一副不和他计较的样子。王老师得手一次,见对方没反应,就接着挑衅,不断地拿汪汪狗往脸上、鼻子上、耳朵后,脖子里来来回回地骚扰。郭汉终于忍不住了,“唿”地站了起来。王老师立即笑着,快速跑着躲开。郭汉好像只是想吓吓他,并不追赶,笑着继续坐下。王老师连着得手两次,没有挑起事端,仍不甘心,越发洋洋得意,继续侵略。这一次不是一根汪汪狗了,而是两根,三根……
常言说得好,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面对一而再,再而三,不断挑战自己的底线,郭汉终于忍无可忍,跳起来开始追赶。王老师笑着拼命地转着圈跑。其实郭汉并没有真心想追,只是象征性撵了几步,便放慢了脚步。但王老师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反而像不受控制般越跑越快,越转圈儿越大,一点也没意识到危险正在向他袭来。
山里的梯田本身就窄,也不过两丈来宽。王老师作为盲人,眼睛看不见还这样快速地在地里奔跑着转圈儿,且越转圈越大,越来越靠近地边。我发觉苗头不对,赶紧大声制止:“不敢跑了,快停下来,危险!”
但王老师像着魔一样,根本无视我的警告和提醒,也察觉不到郭汉早已停下不再追了,自顾自疯狂地跑。不是讲迷信,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左右着他,把他推向危险的边沿。
第一次警告无效,再次紧急提醒:“到地边了,小心掉沟……”说时迟,那时快,“掉沟”二字还没出口,就见王老师已经旋到地边,身子向外一趔趄,“呼”地一下便没了踪影。随着“朴嗵”一声,我的大脑“嗡”地一声,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短暂发懵后立即反应过来,打个箭步跑到地边,来不及多想,也不管高低深浅,一咬牙跟着跳了下去!
有的笑了,一对二球!你老师疯了,不要命了,你也不想活了?摔死没有?哎,摔死今天还会在这跟你讲这个故事哩?人人都怕死,但到了关键时候,紧急时刻,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你想,老师如果出个事儿,我这徒弟能囫囵吗?如果老师没了,我这徒弟还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吗?要死不如跟着一起死吧,那时候反正就是这么想滴,哈哈。
谢天谢地,真是高运气!幸好这麦地下面还是一块梯田,如果是深沟,不说粉身碎骨,恐怕想活着比登天还难!梯田之间的高度不过一丈来高,虽然很陡,但也不是垂直的,直上直下,还是带点坡度的。王老师并不是实打实地摔了下去,而是连滚带栽地滑了下去。好在下面是松软的麦地,又有麦苗做铺垫,减少了不少冲击力。以至于老天还给了王老师一次让他躺在麦地里“哎哟,哎哟”呻吟的机会。
顾不得自己蹿得腿疼,赶紧去扶老师。王老师还没等我扶,就已经先坐了起来,衣服上,脸上都是土,真可谓“灰头土脸”啦。我一边帮他拍打衣服上的土,拂去头发上,脸上的灰,一边忙不迭地问:“啥样儿,有事没?”王老师勉强地挤出一点笑,以示让我放心:“没事儿,别动我,叫我先歇歇。”
坐了一会儿,我说:“先起来转转,活动一下,看有没有事儿。”说着慢慢地扶他起来,走了两步,见没啥异常,就绕到坡度比较缓的地方连拉带扯地把他拽了上来。
郭汉在上面早已上蹿下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想团团乱转,可又不敢,眼看不见,怕掉沟呀!发觉我们上来了,一问,走路正常,没啥大事儿,才算松一口气,便开始数落起王老师:“老哥,不是要说你。今天我招你,惹你没?是你三番五次寻事儿,我还没撵呢,你自己先跑。可不能怨我给你撵下去啊。”
王老师不敢犯犟,忍着疼,一连声地苦笑着说:“怨我,都怨我。哎,今天真是侥幸,要是摔到深沟里上不来,还叫你们回去给俺家里没法交差哩。”
见郭汉训王老师,我忍不住也想发泄几句。谁说徒弟不敢训老师?那是没遇着茬口儿,没逮着机会!并不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说句不太恰当的话:人怕输理,狗怕夹尾。就怕老师真正输理、犯错的时候。往常一直都是被训对象,受老师的气,吆喝来吆喝去的。今天好容易逮着个机会,揪住了老师的软肋,像抓住了有尾巴烧饼,也日噘老师几句过过瘾吧。于是,理直气壮地朝他吼:“还知道怨你?当老师哩,有个老师形儿(形象)没有?人家郭老师不给你毛捣,你手恁狂做啥?不叫跑,说你偏不听,摔你屈不屈!要是给你摔不中了,俺们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知道了是你自找的,外人不知道,还以为是俺们图财害命把你推下去呢!”
一贯强势,训我们如家常便饭一样的王老师,想不到也遭挨徒弟训的“报应”,还不敢发作,摆老师架子。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红着脸,咧着嘴,似笑非笑地赔不是。真令人解气,开心哈。
郭汉又在一边儿说风凉话:“你家(促读niá)老师主要想量一量沟有多深哈。老哥,苦去求啦,跌到徒弟嘴底下了吧?看你还漏不漏[②]!”
王老师自知理屈,不敢反击和狡辩,只有认错的份儿。也知道郭汉是故意拿他开涮,逗大家开心的。大家哈哈一乐,担心、紧张的气氛稍缓和了些,王老师一笑,似乎腰的疼痛也减轻了不少。
说笑归说笑,正事不能忘。我问:“老师,现在怎么样?走路耽误事儿吗?再歇一会儿,还是现在就走?”
王老师手托着后腰,活动了一下:“没事,能走路。”
郭汉说:“那赶紧走吧,趁伤气还没散开,到村里看看哪有卫生室,先检查一下有事没事儿。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不能在路上耽误。”
接下来还算顺利,我们到了村里,所幸这个小自然村还有一个小卫生室。找大夫看了一下,主要是伤气,没有大碍,开几包和血化於的消炎药,买一瓶正红花油涂抹。很快找到了队长,安顿下来,吃罢中饭,躺到床上休息。
王老师的伤气好像扩散开了,腰疼得躺也不是,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在屋里游行示威似的来回走动,说:“不中啦,晚上坐不到那,无法拉弦子啦。武成,晚上拉主弦就靠你身上啦。”
我听了暗自窃喜,终于逮着领主弦的机会啦,早知道早点让王老师掉沟该多好哈。心里这样想的,嘴里却说:“可不敢,我会弄成?王老师抓紧吃药,药水多抹几次,晚上坚持一下应该没事儿的”
“我说你中就是中,放心大胆拉吧!早点做个思想准备。”
我心里乐开了花,话都说到这,晚上领主弦是板上钉钉的事啦。就暗暗地攒着一把劲儿,迎接第一次领主弦的挑战,好好珍惜这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不让老师们失望,尽可能地把能力发挥到极致,给老师们提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吧。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晚上开书时,王老师竟然改变了主意,强忍着腰疼,坚持着坐上拉主弦的第一把交椅,丝毫没有让我坐正位领主弦的意思。一边坐卧不安,轻声喊疼,一边却占着弦子死不丢,连让让我的机会也不给。哎,这不是捉弄人吗?害得人家“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这叫啥事呢!
如此的食言,说话不算数,临时变卦。我表面上还得装出对王老师爱岗敬业精神的敬佩,还得为王老师害怕我拿不下来主弦,不想让我作难,带病坚持工作的义举而感激涕零。心里却恶恨恨地说:
“摔你哩轻!”
哈哈,这算不算“阳奉阴违”呢?
[①] 加是:听音记字。各地方言有不同的意思。见下文。
[②] 漏不漏:新安方言中挖苦人的土话,此处的“漏”系“漏能”,卖能,故意炫耀、展示自己本事。“漏不漏”是漏能不漏能的省略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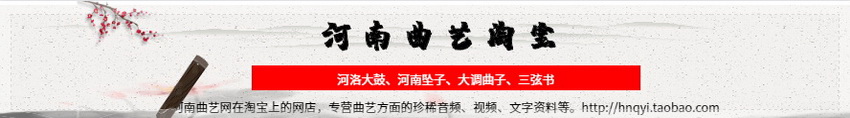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