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十九
夜走百里为听书
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老师临时改变主意,不让我领头弦,一直心存芥蒂。常悻悻地想,怪不得当初在我们村说书时,王遂厚和他为这事儿差点打了起来。人家认为老师保守,害怕徒弟学得快,不无道理啊。但事隔多年,直到经历风雨摔打出师之后,回过头来再想想,老师的做法也许是正确的。因那时尚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拉弦儿的功夫已经到家了,可以独当一面了。殊不知河洛大鼓的唱腔随意多变,其伴奏也是充满变数,稍微有些特殊变化,岂是我一个刚入门的生手能应付得了的?如果到时候“凉了场”,“掂了弦儿”,出乖露丑,下不了台,岂不是丢人更大?与其让徒弟当面出丑,还不如老师自己忍着、受着、扛着呢。每想到此处,便释然了。
哈哈,为啥要重提此事儿?我害怕有人看了这件事儿说闲话,传到俺老师耳朵里,影响师徒关系。这样自圆其说地解释一番,即使老师知道了,他也说不出来啥哈。
不提啦,这都是麦前的事儿,已经翻篇了。春天灵宝说书,虽然开头吃了些苦头,但后来尝到了不少甜头。灵宝的山,灵宝的水,灵宝的父老,灵宝的胡卜,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然,说句更实在的话,那就是灵定的书价比新安县高一点儿,我们可以多挣点钱。王老师毫不犹豫地决定,夏天继续上灵宝说书去!
我忙着收麦,老师一点也没闲着,为二次征西做充分的准备。汲取了年初的教训,通过跑腿、托关系,及早从新安县文化局弄出来一张演出证明。春天在灵宝说书时,大多地方都嫌我们说书的人少,不热闹,不红火。我们也深有体会,尤其是大舞台上演出,显得空落、单调。为此,王老师决定:一是增加人员,扩大阵容;二是增设乐器,加强装备。把队伍武装壮大,以适应灵宝的演出市场。
计划归计划,实施起来不容易。首先是演员问题。灵宝锣鼓书中大都有年轻漂亮,才艺双全的女演员。人家女演员往台上一站,便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十分养眼,尤其是能博得年轻人的眼球,未及开口,先赢了几分人气。可新安县如此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哪里找去?
那个年代,新安县农村相对封建、落后。尽管在三教九流里,说书的属于“上九流”,被尊为说书先生,有别于“王八戏子鳖吹手”的,但人们根深蒂固的潜意识里,却把说书和唱戏混为一谈,认为不是体面的职业,甚至还有“和戏子一样,死了都不能入老坟”的错误认知。新社会,新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转变了不少,实际上剧团并不乏女演员,并没有人认为丢人现眼。但说书行里仍然守旧,男子学说书尚且觉得是丢人的事儿,何况女子?故在新安县一带,女的学说书可谓凤毛麟角,偶有想学者,大多不被家庭支持而半途而废。当然也不是完全如此,比如新安县仓头仙人沟的侯秀英,就克服了家庭干涉的重重阻力,毅然学了说书,且学有所成,在新安、孟津一带已经闯出了名气。
找侯秀英搭班合作去灵宝,王老师不是没考虑过。侯秀英是新安县河洛大鼓行唯一学说书成功且已出名的女艺人,物以稀为贵,人以缺为尊。人家到哪里都相当吃香,说书生意稠得很。正走红时,想找侯秀英搭班合作的艺人趋之若鹜,能排成队。别看我们都是仓头公社的,却只是听说过,没见过面。王老师、郭汉他们与人家也没什么交集,排号也挨不上啊。王老师深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庙小,容不得大神,所以直接打消了去请侯秀英的念头,还是自己解决吧。
王老师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尽量用自己人,不找外人,免得担风险,落不是。就让自己的老四兄弟王浩子来充当人选。
王浩子和我年龄一般大,都是属兔子的。自幼害小儿麻痹,腿落下残疾,干不了重活,王老师就教他学拉弦子,水平和我不相上下。他上学不多,记性差,嗓子不好,且有点舌头大,吐字不清,他哥教了几个书帽,很难流利地唱下来。所以只好待在家里,王老师一直没能把自己的亲兄弟带出来。这一次机会来了,就随我们一块上灵宝说书。
人员安排好了,下一步就是装备。王老师不但把王浩子经常拉的枣木做的坠胡带上,另外还配备了板胡、二胡。拿板胡干什么,还唱豫剧?按王老师的话说,乐器也得“宽备窄用”,多捎几样乐器,以备不时之需。尽管我们谁也不会唱豫剧,高兴时候拉拉开心一下也是好的。考虑到西边灵宝爱听锣鼓书,便也带上了大锣、堂锣、钗等戏曲的打击乐器,也准备模仿人家锣鼓书的那一套儿,不管会打不会,得有这套家伙儿,晚上开场前敲打着热闹热闹啊。
收罢麦,一切筹备就绪,按“七不出门,八不归家”的说法,选定初六这个良辰吉日,人马聚齐,整装出发,直奔灵宝。
一路顺风,有了春天灵宝之行的经验,直达灵宝县城下火车,省去许多弯路,一嘴啃到豆馅上。直接找到了县文化局,很顺利地把证明换了出来。恁快?主要是我说得快,把路途之上的琐碎事儿都给省啦。你没听说书人常说:“飞机快,大炮快,都赶不上说书的放卫星。哪怕十万八千里,搁不住嘴角冒股风!”到灵宝换个证明,也就是俺说书的一句话的事儿。和春季那张演出证明不同的是,原来的是一张纸,这次是红彤彤的一个大本本儿,上书 “演出证”三个烫金大字,显得高档大气,很有派头。
有了春季的演出经验,一切都变得轻车熟路,很容易便靠好了首场演出。照例还是文化广场,文化舞台,扩音设备,蜂拥而至的观众。但这阵势我们已经见得多了,习以为常,上舞台已经“胜似闲庭信步”了。再说和麦前比,我们的人多了,装备加强了,更增加了些底气和信心,怕什么?
按惯例,上场来先来一个“闹场”,以招徕听众。搁往常,都是由徒弟一个人 “击鼓带板”地敲,老师们在旁边坐着吸烟、喝茶,或收拾工具,作准备工作。现在不同了,我们人多,还有锣鼓家什,有啥说啥,当然得派上用场啦。
我们这些人都是说书出身,没有唱过戏,哪懂得戏曲中的锣鼓经?初次接触锣、鼓、钗这玩意儿,尽管出发前也练过,还是不得要领,不知套路,无从下手。但舞台上来不得半点犹豫、推让和畏缩,让观众看出来我们这几个人是外行、“白脖儿”,假充行家的“冒牌货”,岂不是网包提猪娃儿,露蹄儿啦?
王老师果断地分派:自己掌鼓板,郭汉掂大锣,王浩子敲小堂锣,我拍钗。然后各执其事,便开始敲打起来。七寸书鼓既充当戏曲中的边鼓儿,也变成了武场中的大堂鼓。王老师用双鼓条击鼓,引领着全场,我们就跟着节奏胡乱地敲了一通,听起来“叮叮咣咣”的,倒也十分热闹。
看着我们一本正经地乱来一气,感到既滑稽,又可笑。这哪里是开场锣鼓呀?咋听着和我们老家农村来的耍把戏儿、玩猴时敲的差不多。如果在老家听到这种锣鼓声,还以为是来了一摊儿玩猴的呢,绝对不会想到是说书的在瞎胡闹。
常言说,内行听门道,外行看热闹。虽然我们所谓的“锣鼓经”不在路数,是“野干家儿”,可观众之间真正懂的内行又有几个?只不过是热闹一下而已。尽管灵宝的观众也不是好糊弄的,听出来和他们熟悉的锣鼓书不一样,面带疑惑,但“三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还以为我们的“东书”的锣鼓点儿就是这个打法呢。
有了演出证,无异于“尚方宝剑”。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每到一个大队,红本本一亮,都会受到热情招待,演出非常顺利。但这把“尚方宝剑”并不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的,也有不好使,卡住壳,打住车的时候。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即使亮剑,也吓不住人家,照样不尿你。
那天,我们到一个大队,像往常一样,找到了大队支书,递上了演出证。支书看了一眼就还了回来:“对不住啦,你们来晚了,已经来一摊儿锣鼓书,安排好晚上演哩。”
支书这一说,我们才明白。怪不得进村经过村中心热闹处时,听见有人悄悄议论:“咦,又来了一摊儿说书哩。”原来两班说书的弄“顶茬”啦,碰到一个村子里了,但赶早不赶晚,手快打手迟。人家先来一步,占尽先机,把后来者的位置给挤丢了。
眼看煮熟的鸭子成别人的了,郭汉还不甘心地缠支书:“沟是沟,河是河,他是他,我是我,他们是锣鼓书,我们是东书,口味不一样哈。支书,他们演他们的,我们演我们的,互不耽误事儿。”
支书摆摆手:“哪有这一说?不可能的,就一个文化大院,一个舞台,叫谁演不叫谁演哩?两摊儿说书的,叫群众听哪一摊儿的?别说啦,等下次吧。”说着转身就走。
郭汉还想撵上去再说几句,被王老师制止:“算啦,多说无益。咱们换地方吧。”大家背起行李,悻悻地离庙。郭汉仍然不服气地嘟囔着:“球,凭啥兴他说(书),就不兴咱说(书)?不中今黑不走啦,给他们别[①]着唱,怼一回!”
王老师怼道:“你是凭跑哩,还是凭咬哩?恁啥跟人家斗?是比人家人多,还是比人家长得好看?江湖规矩,先到为君,后到为臣。没人家来得早,就得退让,不能跟人家争。再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人家当地的,咱是外来的,和人家斗,有啥光沾?安安生生爬走吧。”
经过文化大院的大铁门时,我不由得往里边多看了一眼,见大舞台上摆着桌子,上面放着各种弦子和笙、笛,地上有乱七八糟的锣、鼓、钗等。不用猜测,肯定是人家锣鼓书的一套演出工具,已经摆在舞台上了。舞台下面东侧几间休息室里,有几个人进进出出,肯定是锣鼓书的演员啦。忽然眼前一亮,从屋里婀娜多姿地晃出一个既年轻又漂亮的女演员。她二十来岁上下,细高挑,上身红西装,下身穿着极为流行的白色喇叭裤,搭配着乌黑锃亮的高跟皮鞋,一头烫过的秀发形成“披肩波浪式”,浑身上下透露出一种高贵、洋气。虽然离得较远,看不清人家姑娘姣好的面容,但从侧面来看,标准的S型曲线,足以博人眼球,引人驻足。只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已经被吸引得“驻足”了,只顾扭脸回头,竟忘记了走路。
王老师已经发觉我走路异常,越走越慢,想停下来,又感觉我在扭来扭去地看。就一边使劲把我往前推,一边说着:“武成,你脖子上安轴承啦,还是咋的?转来转去,转啥哩转?都不会好好走路!”
我如实汇报:“王老师,我看见人家那一摊说书的啦,在文化大院呢。人不少,还有一个年轻女的,长得可漂亮啦。”
郭汉一听有女的,来了精神,眼翻了翻:“走,怼进去看看,会会他们!”
王老师脸上笑了一下,似有所动,但立即又沉了下来,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看啥哩看?女的没见过?人家把咱生意给顶了,还腆着脸去见人家,不知啥叫没意思。”
说实话,对锣鼓书我也挺感兴趣,尤其还有女演员。就小心翼翼地说:“王老师,你不是说过江湖规矩?同行见同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后来者不是得拜访先到者,外地的得拜访当地的?”
王老师训道:“你懂个屁!那是咱洛阳一带的规矩,东边的菩萨到西边还能灵?一个地方一个规矩,一个行当一个规矩。人家是锣鼓书,咱是大鼓书,行道不一样,路数也不同,有啥可拜访哩?都是成色瞎,见女的走不动,不用这呀、那呀地找借口,赶快走!”
话说到这了,谁叫人家既是老师,又是领导呢?老师永远都对,领导永远正确。别说徒弟得无条件服从,郭汉也没了脾气。虽有不舍,也只得离去。
合该今天不顺,两班碰到一块了。按江湖迷信说法,同行之间两班碰到一块儿是大忌。江湖上有“人不亲行亲”的说法,却又有“同行是冤家”之论。看似自相矛盾,却各有各的道理。同行之间,追本溯源,极有可能“五百年前是一家”,同师、同宗、同源。既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行见面一家亲,彼此沟通交流,增进感情,其乐融融,此谓“人不亲行亲”也。然而同行相遇的弊病也显而易见,那就是争夺饭碗的尴尬,生意会相互造成影响。江湖人赖以生存的饭碗就是命,为了争饭碗,不惜同行反目,自相残杀,故有“同行是冤家”之无奈。
就拿今天的事儿说吧,我们从西往东来,而另一班锣鼓书则是从东往西去。两班相遇,我们再往前行,走的就是人家已经走过的路,我们再去说书,就是收二茬麦,做重茬生意。道理很简单,人家嚼过的馍,吃着还会香吗?生意肯定受影响。对方也是一样,虽然眼下他们占了先,抢了我们的生意,但下一步再往前走和我们一样,重复我们走过的路,生意也好不到哪去。
果不出所料,当天我们跑了几个大队,得到的答复几乎一样:我们已经刚说(书)过了。郭汉死缠烂打的手段使尽,还是不能改变最后的结果——不说(书)!王老师甚至把“杀手锏”红本本亮出来,扬言:“我们有证明,不说也得拿钱!不然俺们找文化局去。”人家不吃这一套:“有证明咋着?不说还是不说,要钱没有!有本事你们去告[②]我们吧,告到哪,请到哪!”冷冰冰地给顶了回来。
我们硬,人家比我们还强势。制胜法宝失灵,大家没了脾气,灰溜溜地败下阵来。有人笑话:你的王老师不是说过,只要有证明,对方不让演出也得拿钱吗?怎么拿不到了?唉,有本事你来试试!上面有规定,有政策不假,但情况不断地变化,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常言说,民不告官;俗话说,胳膊扭不过大腿。咱一个外来的穷艺人,和人家一个生产大队斗,有啥好果子吃?拿鸡蛋碰山,碰得过吗?退一万步说,即便官司打赢了,赔咱一场书钱,能耗得起时间和功夫吗?有这时间和精力,还不如多说一场书啥都赶出来了。要不然,人们怎么说:小气儿好生呢?人都说,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何况我们为了一场书不至于屈死吧?
既然不能硬顶,只有避让。看来在这附近是联系不到书场了,王老师和郭汉商量一下,走路太难,决定坐车跑出川口公社的范围,然后重打鼓,另开章。这一坐上车,一跑便是四、五十里路,终于摆脱了那一班锣鼓书的影响。等我们成功地靠住了书场,安置妥当时,已经是傍晚了。
早在没来灵宝之初,对锣鼓书早有耳闻,却未曾目睹。听王老师说起锣鼓书的奇闻轶事,神乎其神,早已对其艺术魅力充满期待。前半天好容易碰到个机会,几乎和锣鼓书来了个面对面,却因为生意上的忌讳,不得不擦肩而过,好不遗憾!走在路上,坐在车里,脑子里的几个锣鼓书艺人,尤其是那个漂亮的女演员在大脑里来回晃悠,挥之不去。以至于晚上说书的准备工作也没心绪,丢三落四的,答非所问。王老师发觉了异常:“武成,你的魂叫别人钩走啦?无精打采哩。”
既然问了,我就吞吞吐吐地说:“王老师,能不能请个假?”
王老师吓了一跳:“咋,病啦?”
“心病。”郭汉笑着插嘴,“不用说是见了锣鼓书班里那个大闺女,引诱得走不动路了,想出来的病。”
见郭汉老师出息我,也没做过多的辩解,只是笑笑:“也不全是。只是没听过锣鼓书,特感兴趣,老想听啊。王老师,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我想今晚上再拐回去听听人家的锣鼓书是个什么样子的。”
王老师差点跳了起来:“你疯啦!你知道这个大队离那个村有多远不?”
“算过了,四、五十里。”我回答。
“来回百十里呀!知道光路上得走多长时间不?七八个钟头啊,跑死你哩!”
“没事儿,我路上跑快点儿,赶到那听一会儿,哪怕是听几句哩,就立即赶回来,也算是听过锣鼓书了。”我仍固执地请求。”
“让他去吧。想去呢,心不在这,书也说不好。”郭汉再次搭腔,“是他跑路哩,又不是咱跑。去听听也中。不然说起来来灵宝一趟,连锣鼓书是啥样也没听过。孙子还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哩。去听听,对咱说书也有好处。”
嘿,别看郭汉老师不识字,《孙子兵法》还知道一点哩!话说到这了,王老师也松了口:“管你哩,想去你就去。能摸着路不能?可别摸丢了,明天不用说书了,到处贴寻人启示找人,可麻烦透啦。”
我如获大赦一般松了口气:“放心吧,老师,我一路上已经查看好地理位置了。那个村子在铁路边上,咱这个村也离铁路边不远。顺铁路走,只有东西方向不迷,牢记两个村的位置,就错不了。只是你们给我留好门儿,别后半夜回来叫不开门,进不去屋。”
王老师感叹:“我的老天爷呀,原来走这一路都做着拐回去听书这锅饭哩。那快去快回吧,赶早不赶晚。”
确定了方向和目标,我沿着铁路几乎是一溜小跑地赶路。人们计算过,正常情况下,步行的速度是每小时十里。五十里路得五个小时?赶到时黄花菜都凉啦!人家刹书了,还听个屁!不行,速度得加快,时间得提前。有的说,你说书的不是嘴快吗?一张嘴可到啦!光动嘴不动腿中毛用!咱不是如来佛,吹口气到西天了;也不是孙悟空,翻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那都是吴承恩瞎喷,路是跑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说再多也枉然,开跑吧!
好在老天爷还照顾我,赐一股凉爽的东风,在背后轻轻地推着,给我散热,与我助力,伴我同行,使我得以一路顺风。身后时不时传来火车沉重地吼叫,车轮撞击道轨的声音,听起来仿佛在喊“快点儿、快点儿”,然后呼啸着擦身而过。快不了啦,和火车赛跑,打死也跑不过哈。
等气喘吁吁,浑身冒汗的赶到地点时,一阵阵的锣鼓声已经飘进耳朵,吸引我进了文化大院,锣鼓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始了。
舞台正中放着一张大八仙桌子,桌子后谓之“上席”,坐着一人,五、六十岁的样子,左膝上放着一把四弦。头一次见到四弦,长得和低音大二胡的样子差不多。不同的是二胡只有两根琴弦,一张弓,这玩意儿竟是四根弦,琴弓的马尾分为两束分别穿行于一、三和二、四弦之间。演奏出来的是双音,听起来就好像两把二胡在合奏。左脚蹬着左桌角绑的脚蹬梆子作为节奏。脚蹬梆子和我们河洛大鼓的大致一样,都是在架子上装一个和尚念经常用的木鱼。大锣、小锣分别放置在桌子上的两个锣架上。锣架酷似河洛大鼓用的木制三角鼓架,不知是锣鼓书借用河洛大鼓的,还是河洛大鼓借用锣鼓书的。两个锣架之间的钗垫上放的也不知是属于铰子,还是钗。说实话,钗和铰子长相差不多,说法也不一致,还真不好区分。
后来才知道,桌子后面这个位置可不是一般锣鼓书艺人能坐得了的,能占住这个位儿的大都是掌舵的头头儿,师傅中的师傅,高手中的高手,在整个团队中统领全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称为“坐帅”。其他所有艺人都如众星捧月般地分坐两边,或操琴,或执板,或击鼓,在“坐帅”的指挥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整个场面,俨然有序,颇有元帅打坐中军大账,众三军排列两边的阵势。
“坐帅”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没有“两把刷子”,没有搁哪哪中,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多才多艺的本事,岂能震得住全场?这个“坐帅”手、足、口、目、耳并用,一刻都不能闲着。你看,左脚踏板,左手执琴,右手拉弦儿,抽空儿还得侍弄桌子上的锣、鼓、钗,目顾左右,耳听八方。连拉带唱,连敲带打,时不时还要站起来吼上两嗓子。忙而不乱,紧而有序。如此精绝的技艺,令人叹服,难怪时不时下面有人鼓掌喝彩。
锣鼓书的七个人都是个顶个的,似乎没有“雪儿[③]”。每个人都担当着重要角色,并非可有可无。每人各执一样乐器,既是演唱者,也是伴奏者。每个人都有戏剧上的角色分工,一人一角,或一人多角,时不时地跳进跳出进行角色切换。该唱的时候停下手中的乐器演唱,该别人唱的时候则立即又操起了手中的乐器伴奏。团队之间,相互协调,配合默契,可谓风雨不透,滴水不漏。
特意多留神了一会儿那个漂亮的女演员,发现七个人中,就她的角色不太重要。她没有乐器,手中只是拿了一对干梆子,跟随着节奏敲。热切想欣赏一下唱得怎么样,结果她的戏分似乎很少,害得我眼巴巴地盼了半天,也没见张嘴唱,只是该需要呐喊助威的时候,跟着大家一齐吼两声,仅此而已。虽然有点小失望,但毕竟舞台上有如此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如同鹤立鸡群,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锣鼓书增色不少。唉,别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啦,想想我们新安县的河洛大鼓,上哪里找这么漂亮的年轻姑娘?
你别笑。可惜那时信息闭塞,孤陋寡闻,眼光狭隘,见识短浅,未能知道巩县河洛大鼓届的五朵金花——牛会玲、韩淑玲、李新芬、黄金焕、王春红,群芳斗艳,才艺精绝,哪一朵不比当前舞台上的这朵强?只是无缘拜会罢了,认识她们都是以后的事了。
听惯了河洛大鼓、河南坠子,初听锣鼓书,别有一番风味。说书,具体到锣鼓书,与其是“说”,倒不如说是吼、唱。演唱者浑身都是戏,把全部激情都投入到唱腔里,尽情尽力的演绎,畅快淋漓地发泄。锣鼓书,具体到听众,与其说是听书,倒不如说是“看书”。这种说唱艺术很大程度上具备戏曲的特色,不但重唱功,更重做功。虽没有大幅度夸张的舞台表演,却表情丰富,动作和姿势优美,能吸引观众不但想听,更想看,从而达到视听兼备的效果。
锣鼓书虽然是说唱艺术,属曲艺范畴,但唱腔风格上极具黄土高原的陕西民歌色彩,高亢明亮,穿云裂石。说是唱,倒不如说是“吼”。唱到激情处,情感喷薄而发,将音符一下子送入云端,跳起来竭尽全力地大吼一声,所有伴奏者立即站起,连吼数声,此起彼伏,互相呼应。其情绪激越豪迈,引人奋发,热闹处,引发台下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台上的人疯了似的,忘我地,激情地演绎;台下的人傻了似的,痴迷地,忘却自我地跟着演员的感觉走,沉浸在热闹中。台上的吼叫声,台下的叫好声,喝彩声,连成一片,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欢快的海洋。
人都说: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这话恰如其分。可谁又曾想到,谁又会注意到,在一片忘我的欢呼声中,文化大院角落里,阴影下,有一个傻不拉叽的外地说书人,夜走百里,跑断腿,磨烂鞋,做贼似的悄悄躲在靠墙一隅,怕人发现,为的就是来听一场锣鼓书!
这该是疯子,傻子?还是用河南话说的:神经蛋,囟球货[4]?!
[①] 别:河洛方言,比赛、竞争之意。
[②] 告:此处是“告状”之意。
[③] 雪儿:江湖行当中指没有技艺,或技艺不高,不能独挡一面,只是凑个数,顶个场面,可有可无的人。
[ 4 ] 囟球货:河洛方言,又作“欣球货”,囟、囟球、囟球货,都是指憨傻、缺心眼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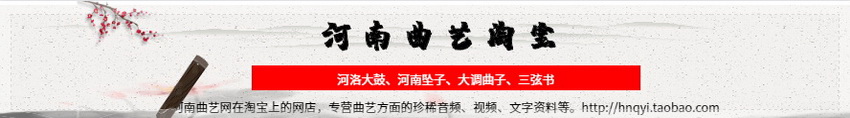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