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十二
书帽《王婆骂鸡》里,王婆咒说书的“背着弦子背着鼓,一年四季好生意。”其实说书人“一年四季好生意”是随口打哇哇的说法。准确地说,说书一年只有三季:春季、夏季、冬季。咋回事儿?把秋季给吃啦!不是,你听我说。夏季说书说到秋熟了,回家收秋、种地。秋季又收又种,农活又多又杂,持续时间很长。先是收玉米大豆,花生芝麻,谷子高粱等杂七杂八的秋作物,继而贮草灭茬,上粪施肥,拉犁扯耙,犁地耩地……前后差不多得月把儿时间,来不及喘口气儿,西风起,天转凉,一场秋雨一场霜,天敖住了,开始着手刨红薯。晒成片儿,磨成(淀)粉,入红薯窑等乱七八糟的事儿又是一二十天过去了。待到萝卜、白菜收回,贮藏完毕,早已进入了冬季。你说秋季有说书的空隙和时间吗?所以,说书生意一年只能按三季,秋季不能算。
一九八一年的夏天,跟老师学徒只出去了一季,经历了繁杂的秋季,到了冬季该出门的时候,情况有了变化,我被王老师给“甩”了。你别多想,可不是“牛大抵牛王庙”,扣老师“豁儿”,掰捏老师毛病,被老师给揣了。是“井里边放炮——有原因(圆音)”啊。
原来王老师在寺村又收了一个算卦方面的徒弟,叫郭爱民。
郭爱民的年龄和王老师不相上下。早年在修寺村大桥时,炸药、雷管出了事故,意外爆炸。他虽然捡回了遍体鳞伤的一条命,但失去了一双眼睛和一只手。夏天在寺村说书时,郭爱民已经和王老师拍得很熟了。他对说书也很感兴趣,想学,但没有眼睛倒不说,关键少一只手,弦子没法拉,钢板没法打,只能表示遗憾。收秋期间,经人说合,拜王老师为师,学习算命批八字技艺。双方立下字据,由徒弟郭爱民聘请王新章上门专业授艺,管吃管住,行师徒之礼,待尊师之道。学艺时间为三个月,讲定酬金二百元,期满钱足,概不扯皮。
教徒弟三个月,刚好一冬过去了。三个月二百块,一个月六十还多可是高工资啊。在八十年代,木匠石匠,说书卖唱等行业按日工算,都是每天两块钱工资。如果搞价钱,优惠便宜,辞让,尽义务等,每天就一块多点。就这还是干一天算一天,刮风下雨,头疼脑热,各种各样预料不到的事儿都会耽误。如果这一天没有干成活儿,那就一分钱也没有,还得倒贴饭钱哈。这样算下来,就拿说书来说,哪个月也说不了三十天吧?生意好一个月二十来天就不错了,要是生意不好,场次不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就更惨了,一个月三场五场,十场八场的也不是没有可能。总之,说书生意再好,一个月也落不了六十块钱。王老师找这个教徒弟的活儿多轻松呀。不用奔波劳累,说了这场愁那场,过了今天愁明天;不用整晚整晚地伸着脖子,扯着嗓子吆喝,惟恐书说不好,观众不满意;不用看眉高眼低,尝酸甜苦辣,上门生意难做,看脸色,听话头了。被请到家里,坐在屋里,风刮不着,雨淋不到,好吃好喝招待,当神一样敬着,风雨无阻,三十天不间断,每个月六十六块六毛六分六,固定工资,铁饭碗,不,应该是金饭碗哈。凤凰都往高处飞,有这样的好事儿,谁能放着清闲自在的金饭碗不端,跑出去吃苦受累地去端说书这个破“要饭碗儿”?该明白王老师为什么把我给踢了吧?人家“另有新徒”啦。
收罢秋,种完地,拐郭庄捎上郭汉老师,风尘仆仆地赶到王老师家中时,得到的却是上面的结果。真是皮球上戳一刀,泄气。郭汉老师不乐意地埋怨:“老哥,你弄这是球!只管自己去挣大钱、巧钱哩,把俺俩都给撂一边啦。我倒没啥,得罪不了,把你徒弟往哪安置?人家跟你学了一季,现在你躲在一边儿去教算卦,挣清闲钱了?你得给人家念个经,有个交待吧?”
王老师笑着一个劲儿地赔不是:“汉儿,我知道这事办得不老妥当,可都是熟人,抹不开面子。再说合同都立了,不能反悔呀。不过你俩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跟河清哥打了招呼,今天冬天恁仨人先搭个班儿,厮跟[①]一季儿。明年春上,铁定咱们就又到一块啦。放心,武成这个徒弟我一定会教到底的。你们看中不中,不中再商量。”
郭汉老师嘟囔着说:“都弄成这缸醋了,还说啥中不中?再说河清哥俺们又不是没搁过伙儿[②],都知根知底的,人都美着哩。只要武成没意见,我没啥说。”
王老师笑了笑:“武成和王河清之间并不陌生,麦前还在他村说过书,早就熟识了。我也介绍过了,没有事儿。”
我笑着说:“王河清老师虽然认识时间不长,相处也没几天,但也挺对脾气的。只是我学到半拉儿,好端端地被老师当皮球一样给踢出去了,把包袱甩给了王河清老师,觉着心里不得劲儿,有点失落感。”
王老师哈哈笑了起来:“又不是永远分开,不再厮跟啦,两仨月以后,咱不是又凑一块儿啦,有啥失落哩?有收得有放,有放就有收。徒弟长时间缩在老师翅膀底下受约束和限制,也不利于长进和发展哈。今年冬天开笼放鸟,抖一下朴噜,自由自在地飞一回,来年春天再收回来。只当是让你实习哩。”
看俺老师说得多美。明明是自己想挣大钱,不得已才把我推托给别人,找的理由还富丽堂皇,弄得好像还得感激他似的。
郭汉老师好像猜透了我的心事,大大咧咧地说:“啥也别说啦,今冬就和河清咱仨人干!新章哥,不用说得恁美,寻着好活儿,挣住了大钱,过了年可得请客啊!要不这事儿不能到底!”
王老师爽朗地笑着:“中,中,中!不要紧。也祝你们今年冬天生意兴隆哈。”
郭汉也笑着回应:“那是一定的。你想着少了你地球可不转啦,没有王新章,俺们就要连毛吃猪[③]哩?是不是,武成?咱们今年冬天干得美点儿,气气你老师。”
打趣了一会儿,我们就辞别王老师,奔王河清家而去。
说实话,一方面少了老师的训教感到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摆脱了老师的约束顿觉轻松和自由;一方面今冬不能和王老师在一起有些遗憾,另一方面却对组织的新班儿充满了新鲜和期待。
王河清,早在麦前俺们村说书时就认识了。长得高高大大的,往书场一站,潇洒英俊,书说得漂亮,说话和气,满面春风,留下了较好、较深的印象。鉴于此,听说能再见到王河清,并能经常在一锅搅稀稠,听他说书常态化,进而能学到更多的精细,岂不令人充满兴奋和企盼?
听王老师和郭汉多次提到过王河清,也从他们口中陆陆续续地听到了不少有关王河清的个人经历。
在新安县河洛大鼓届,尤其是失目的盲艺人中,王河清是几乎唯一的“文化人”、“识字人”。他和王老师、郭汉老师的先天性失明不同,是“半路瞎”的。好多盲者包括俺老师他们在内的都不想承认先天性失明这个事实。有人问起他们:“你的眼看不见是半路的,还是胎带的?”“胎带的”就是出生时就看不见东西,即先天性失明。他们都回答是“半路的”,而不说“胎带的”。问及失明的原因,惊人的一样,都是小时候耍雷管儿崩着的。哪里这么多雷管爆炸事故?之所以不想说自己是胎带的失明,是因为农村人有因果报应的迷信说法,认为是祖上没积德,没办好事儿,才积下后代瞎子、瘸子,哑巴、聋子的。也有“前世做坏事、恶事太多,来世才投胎成瞎子来报应”的言论。既然有这种成见,你想,哪个盲者想承认自己是“胎带的”瞎子?

七十三岁的王河清老师
但王河清却确实是半路瞎的,而且不是千篇一律的“被雷管崩住了”。他上过高中,文化程度搁那个年代不算低吧?毕业后当过几年大队会计,没有两下子能干得了吗?原本已经结婚生子,有了幸福的家庭,美满的日子过得滋滋润润的,谁不羡慕?然而厄运却悄无声息地袭来,二十八岁那一年眼上出了毛病,医学上叫“眼底出血”,后发展成重度“玻璃体混浊”,经偃师著名眼科医院多方面治疗无效,最终导致失明,成了“睁眼瞎”。
常言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夫妻之间,很多能做到“同甘”,却做不到“共苦”。不离不弃都是美丽的爱情传说,现实中凤毛麟角。王河清的失目,不但自己痛苦、绝望,家庭也陷入了黑暗的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妻子几经犹豫、磕拌,最终选择离开,撇下三岁的儿子,狠狠心,跳起腿走了。眼底出血,使身体受到了伤害;家庭的变故,又使心底在滴血。屋漏偏遭连阴雨,行船又遇顶头风。雪上加霜,一连串的打击,一度让他萎靡不振,苦恼万分。以至后来每提到那段历史时,王河清都不愿多说,不想揭开那个沉重的伤疤。
小家散了,大家之中,亲情之间却温暖常在。他的父母,两个兄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陪伴。眼看不见,闷在家中,不是个事儿,得找一个出路啊。失目人干啥都困难,于是他们就想到了说书。
他的两个兄弟通过多方打听、考察,最后认定了离北岳最近的正村东沟村有一个老说书名艺人,叫王振松。就说服动员大哥拜师学艺:“哥,窝在家中苦闷,俺们也着急。眼看不见,干别的啥不中,我看说书是你的事儿。好多说书的都是失目人。你有文化程度,学这个应该不难。不如就学说书吧,不说挣钱多少,起码能出去转转,散散心哈。”
王河清亦久仰王振松之大名,深思熟虑一番,点了点头,目前只有这一条出路了。
王振松系新安县河洛大鼓第三代名艺人,少时先投孟津马甲申学艺,解放后马甲申犯罪被枪决,据说审判时王振松还同老师一起陪过跪呢。后来又投巩县第二代艺人陈有宫学艺。而陈有宫则是偃师河洛大鼓开山始祖段炎的弟子。王振松前辈学艺经历可谓一波三折,正因如此,其说书风格融百家之长,既继承了孟津艺人灵巧欢快的“碎口书”的特点,又汲取了巩县大腔大口之“大口书”的沉稳和厚重,成就了新安县第三代艺人中的佼佼者。他一生中授徒最多,成为新安县河洛大鼓流派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新安县的河洛大鼓艺人毛久常、王赞、冯堆子、冯亭子等都是他的弟子,当然还包括俺老师的老师,我得给人家叫师爷的郭黑蛋。
王河清点头,兄弟们跑腿,很快就说合成了,把老王先儿(王振松)请到家中授艺。一来老王先儿系一代名师,经验丰富,教徒有方;二来王河清有文化,悟性高,且当过会计,记性好,心底清,学得快;三来为了给自己争口气,为了以后的饭碗,只能专心致志,刻苦勤奋地学习。总之,只在家学了半个月,就跟着老王先儿出去说书了。
常言说,人过三十不学艺。王老师说过,尤其是拉弦之类的乐器,讲究“童子功”,十至十三四岁是最佳时机。年龄越小就越好学,指法、弓法流利,反应能力强,接受能力快;年龄越大,指法、弓法就会变得疆硬,不灵活,速度跟不上。我19岁学拉弦时,王新章老师已经嫌学得有些晚了,技艺终究难以学精。王河清却颠覆了“人过三十不学艺”的认知,二十九岁——即将跌入三十岁的门槛时才接触河洛大鼓。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学得非常快。不到半年的功夫,已经具备一定的说唱功底和独立伴奏的能力了。
按王河清自己的话说,虽然命运多舛,遭遇不幸和挫折,但总有贵人相助。王振松就是他踏入说书门里的第一个贵人。
王河清跟随王振松老师仅出去了一季,进步很快,收获满满。但他同老师一样,都是失目人,生活起居,日常住行都需要别人照顾,多有麻烦和不便。王振松老师上了年岁,有时不想外出行艺,遭受颠沛流离之苦,在带徒弟方面已经力不从心。就在这时候,遇上了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新安县曹村黄北岭的河洛大鼓名艺人姜治民。
同王河清一样,姜治民也是新安县河洛大鼓艺人中出了名的“能人”,有知识,有文化,有相貌,有派头。年轻时当过大队支部书记,卸任后偏偏对说书情有独钟,听得多了,见得广了,积累得丰富了,竟自己模仿着学起了河洛大鼓。按乡下农村说法,他学说书没有“经过师”,即没有投拜过师傅,完全靠自觉成才的。但他凭借较为丰富的知识,聪明灵活的头脑,随机应变、幽默谐趣的能力,短短时间,一跃成为新安县数一数二的河洛大鼓名艺人。
姜治民没有正式师傅,所有艺人却都是他的师傅。他博众家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又吸收豫剧、曲剧的一些唱腔特色,融入到河洛大鼓演唱中。他的嗓音宏亮,吐字儿清晰,口齿伶俐,擅唱“碎口”,演唱节奏紧凑,速度较快,是新安县“碎口书”流派典型的代表艺人。他的模仿能力很强,听众说他装啥象啥,装谁象谁。他的扮相潇洒大方,富有“先生派”气质。
他有一个“怪招”,说唱到滑稽处,常常自己“噗嗤”一笑,引逗得观众忍俊不禁,也跟着笑。对于这种逗笑方式,业界多有争议,有的认为是一种观众互动的技巧,有的则认为是一种“贱病儿”(不良习惯)。
姜治民的代表书目有《回龙传》《金镯玉环记》等。七十年代演唱的新曲目《送粮路上》在洛阳地区曲艺会演中获得广泛好评。
姜治民的河洛大鼓得到大多数人的喜爱,录音技术普及后,许多人将他的唱腔录成磁带。有这样一段趣闻:曹村北沟的刘贤忠为了录制他的《金镯玉环记》,三伏天将他请到家中,连续录制8个小时。致使他中暑晕倒,大病一场。
就是这样一个在新安县说书行中举足轻重,很有名气的“大干家儿[④]”,却找到了王河清的门上。
但凡艺高之人,大多恃才自傲,姜治民亦然。常言道,生意好做,伙计难搁。姜治民书说得有名气,但一直没有合适的“弦子把儿”(配合伴奏拉弦子的人)。原因就是高不成,低不就。这年冬天,正“缺住套儿”(缺少配套拉弦的),听说王河清,就找上门了。
一个在家发愁没有合适的人厮跟,一个找不到合适的“拉家儿”。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姜治民就把王河清领了出去。
据王河清后来介绍,姜治民虽然目中无人,一般说书人都不放在眼里,但人家有骄傲的资本,技艺确实让人佩服。且两人的性格、志趣都非常相投,合得来。姜治民并没有歧视王河清是失目人,资格浅,对他非常客气。两人配合默契,得心应手。王河清坦诚地说,自己的调门、唱腔及演唱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姜治民的影响,弦子也得以很好的锻炼、打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凭良心说,是师傅王振松把说书引进门,而真正学艺有成,则与在姜治民那里的实践和切磋密不可分。严格地说,姜治民可称得上自己的半个师傅。
五头梁村与正村北岳相距大约二十来里。我和郭汉老师一边赶路,一边谈论些关于王河清的事儿,寻曹操就说曹操嘛。一路说说笑笑,倒也轻松愉快,不知不觉就看到了北岳村。
中岳、南岳和北岳三个村子均在新安县正村境内。河洛一带的许多地名都会念转音。比如“正村”念作“真村”,“许洼”念作“学洼”。同理,“南岳、中岳、北岳”实际上是书面写法,乡下习惯上却叫“南月寮、中月寮、北月寮” (听音记字)。
北月寮在正村的北面,是一个很大的自然村,呈东西条状分布,从东到西接连不断有三四里长,南北宽则不足半里。王河清家住在村的最西头,很好找,稍微一打听便摸到了家门口,是依土岭而建的半天地窑院。远远地望去,背依大山开凿的三孔土窑作为正窑,其它三面都是开凿进去自然成院墙的,正对“主窑”开凿有外出的通道,聚上一个简易的老式双扇木大门儿。
说话不及,我们已经来到了大门儿跟前,门额上挂着一块伤残军属光荣牌,红底金字,闪闪发光。还没等走到门口,郭汉老师便扯着嗓子喊了起来:“老王哥——,在家秒( ‘没有’促读音miao)?”
大门很快开了,就见王河清摸着走了出来,一边往外迎,一边笑道:“哎哟,汉儿,老远就能听出来是你这一声儿。”
郭汉大咧咧地:“咋?来你家回数多啦,就老远都知道是我啦?”
王河清也说得听着入耳:“哈哈,主要是咱们老美呀。”
他两个打着趣,王河清的父母也热情地迎了出来:“汉儿,看你说哩?这不也是你的家,想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咋会来得多呢?”这时,王河清的三兄弟王清汉三步并作两步地赶了出来,二话不说,跑到郭汉跟前,接过肩上的行李,连搀带拉着郭汉进了大门。郭汉老师一摸便知是谁,又套起近乎来了:“哎呀,我郭汉儿,你清汉儿,都是‘汉儿’,是对法儿[⑤]!咱弟们老对缘法[⑥]哈。”
王老师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同行之间来往,都不准带任何礼品。道理很简单,你来我家带礼品,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去家也不能空着手吧?同行之间,来来去去频繁,如果每次相互来往都带礼品,就会感到非常繁琐、多余,没有意义。于是,就彼此约定,无论到谁家,都不能带礼品。所以我去拜访俺老师,郭汉老师俺们去访王河清,都是俩肩膀抬一个嘴过去的,没有携带礼品的习惯哈。
头一次去王河清家,我们虽然没有带任何礼品,却享受了在农村来说,已经是最高规格的接待礼遇了。一家人,包括父母象迎接贵宾一样来欢迎我们,我都感到真的不好意思了,至亲好友也不过如此隆重地远接高送吧?
大家一阵热情寒暄,好像久别重逢般的亲热,让我插不上话,连个打招呼、问候的机会都没有。直到让到屋里坐定,才论到说话的茬口,怯怯地走到王河清跟前,拉住他的手:“王老师,还认识不?”
王河清,不,直呼其名太没礼貌和修养了,不管怎么论,都应该称为老师。王河清老师立即惊喜般地站起来,反握着我的手:“武成啦不是?咋会不认识哩!想不到咱们又见面啦,哈哈。”
我腼腆地:“王老师,麦前做梦也想不到,今天还会摸到你的门上,更想不到还能成为你的徒弟。以后学说书学得好坏就全仰仗你啦。”
王河清老师爽朗地笑着:“啥徒弟不徒弟的?已经听新章说过了,咱们今冬能搁伙计,真的太美啦!别人不知,我会不知道?你的文化水平比俺们高得太多,我还得向你学习哩。吕蒙正是宋朝一大才子,谁不知道?你是吕蒙正的后代,也是吕先儿哩。哈哈儿,吕先儿,不用客气,咱们相互学习。”
我称王河清为老师,于情、于理、于规矩都是应该的,可他反过来又称我为“吕先儿”,呵呵,这不乱套啦?怪不得常听老师他们说,王河清的脾气、性格太随和了,为人处世,一団和气,从来不好得罪人,没有架子,和谁都能合得来。今天算是领教了,和气到没大没小,没有师徒界限之分啦。
在王河清老师家停了短暂的一天,就深深感受到这个家庭浓浓的亲情味儿,温馨的和谐氛围,文明礼貌的环境。也顿时领悟,之所以王河清老师待人接物,言谈举止,处处文质彬彬,很大程度上受其家庭环境的影响和熏陶啊。
他的父亲不爱多说话,却透着一股军人的气质,有着光荣、辉煌的历史,门上的伤残军属光荣牌告诉了我们一切。母亲勤劳、善良,农村妇女的所有传统美德都能在她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说话,处事儿非常文明得体,招待我们吃饭、休息,热情得就好像对待自己亲孩子一样无间。他的两个弟弟都已各自有了家庭,一大家子挤在一个大院里,从来没有分家的打算。虽然是土院,土窑,但院子里、屋里收拾得井然有序,打扫得看不到一点垃圾和杂物。厨房的灶台,客屋的八仙桌、椅凳擦抹得发明、发亮,一尘不染,到处充满着干净卫生,文明礼貌之风,给人以清新、舒心之感。
据王河清老师后来说,老二兄弟清坡是建筑工头,常年在外包活儿、领工,非常能干,有个性,有魄力。和大哥不同,性格刚傲,却非常敬重兄长。无论再忙、再累,每天晚上兄弟两个都会到大哥屋里坐一坐,问长问短,“汇报请示”,无形中抬高了王河清老师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王河清老师说过,弟兄三个包括父母一大家儿十二口人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个院子里,从来不知道生气和吵架是什么,更没有打架骂人的事儿发生过。两个兄弟媳妇从来没有和公婆红过脸,吵过嘴。这样农村少有的文明和睦家庭真的另人羡慕不已。
置身于这样的家庭环境里,一向爱说粗话,做事粗鲁,性格粗放的郭汉老师受其感染,也不得不收敛一些,装出一副文明的样子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能左右人格,这话一点也不假哈。
第二天一早,我们该上路了。王河清老师的母亲头天晚上就把儿子出门需要带的东西准备得停停当当,把有的衣服,该洗的洗,该缝的缝,该包的包,该叠的叠。看着她披一头白发,戴着老花镜,在昏黄的灯泡下,一针一线地缝衣,又联想到自己的娘亲,眼睛就不觉湿润起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在这个伟大的母亲身上体现个淋漓尽致!天不明就起了个大早, 我们起床时,饭菜早已热腾腾地端到桌上了。
母亲看着我们吃好饭,又亲自为她儿子挑来挑去地拣衣服,亲自看着穿上,前伸伸,后拽拽,一边摘掉前襟上的线头,掸去后背上的灰尘,一边唠叨着儿子不注意收拾自己的身体卫生。在这个过程中,她并没有像其它母亲一样,千叮咛,万嘱托我们照顾好她儿子,但以实际行动做出了示范,一句话都不用说,我们还敢不照顾好吗?这就是老太太的精明之处哈。
儿行千里母担忧。一家人把我们送出大门外,老母亲送我们到岭头上,在我们再三劝她不要再送了的情形下,只得止步,目送我们远去。我们走出了二里地,回首望去,见老太太仍站在晨风里,手搭着凉棚,向我们这边张望,顿感心里酸酸的,暖暖的。
老三兄弟清汉替他大哥背着行李,领着大哥坚持送我们到上庄的柏油马路上,才依依不舍地分手。弟兄手足之情令人动容不已。
[①] 厮跟:河洛方言,跟随、结伴同行的意思。
[②] 搁过伙儿:河洛方言,也称“搁伙儿”,合作、合伙之意。
[③] 连毛吃猪:原句是“死了王屠,连毛吃猪”,指没了王屠夫,就得吃没煺毛的猪肉。比喻缺了某个紧要人物,事情就办不成。
[④] 大干家儿:河洛方言,意指办大事,弄大事的人。
[⑤] 对法儿:河洛方言里,把名字相同的两个人称为“对法儿”。
[⑥] 对缘法:河洛方言,意为有缘分,合得来,脾气相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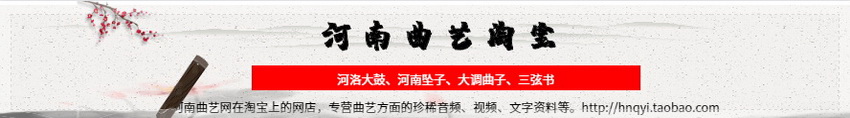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