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十三
我们三人辞别了王河清老师的家人,顺新孟公路一边扯些闲话,一边不紧不慢地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三叉路口。郭汉老师问:“老王哥,走哪个方向?”王河清憨厚地笑笑:“汉儿,咱们仨人你做主,你说去哪,咱就去哪。俺们都听你的。”
早就听王老师说过,王河清说书好、人品好、脾气好,为人特别随和,轻易不会发火,不会跟人争执、吵架,不好事[①],不得罪人,是出了名的“老好好”。这种性格既有长处,但缺点也得明显。生性懦弱,说话办事儿优柔寡断,缺乏魄力,没有主见,不善耍手段,玩计谋,不会随机应变。说书是他的强项,联系说书场次,打外交显然不是郭汉老师的对手。
郭汉老师谦让了一回,也就不再客气了,离了王河清老师的家,粗口就爆出来了:“球,那就听我的,没事儿!今天冬天说书生意不敢保证,但吃的、住的管保不叫受症。”把烟头一扔,脚一踩,朝北边一指,“下北山底下(促读dia)!”
郭汉有令令必行。一声令下,立马启程,往孙都方向至郭庄路口西拐,经范沟,绕郭庄,郭汉老师经过家门而不入,从半坡斜下,穿云水,跨畛河,越梁庄,一路向西,至傍晚已经落脚到北冶南边的张官岭村。有的说,恁快?呵呵,主要是我说得快,路上走得慢,好几十里路,跑了大半天呢,有心让慢慢走,咱慢慢写,恐怕看官耐不住性儿,手一扒拉,滑过去了,万一看得不耐烦,摔了手机,俺可赔不起啊。所以说呀,路上干脆来个一笔带过,几十里的路,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嘛。
八一年的冬天,尽管郭汉老师在北山底下很熟,人脉广,活动能力强,但包产到户的大气个候所致,说书仍然举步维艰,同夏季一样,前半季生意如萧萧的西风,萧条,冷淡。
不记得张官岭好像是说了两天,还是三天,就开始换地方了。下北冶,过滩子沟,上柿树岭,到后骆岭停了一晚,没有联系上(说)书,第二天下涧沟,在上涧村说了五六天,就南上望古垛。
不得不佩服郭汉老师的神通广大,人缘好,到处都结交有熟人、朋友。他说过,保证我们吃住不受症,绝不是夸海口,喷大话,句句都落到了实处。每到一处,不管说书不说书,生意不成情义在,都有落脚点儿,有吃有住。不但吃住不愁,还能享受吃“改样儿饭”住“安乐窝“的待遇呢。
有的问,啥叫“改样儿饭”?改样儿饭也叫“待客饭”,八十年代初,虽然土地连产责任制,粮食打得多了,人们逐渐填饱肚子了,但新安县大山以下,尤其是后山一带吃的仍然很欠,远远达不到现在的小康,仅是脱离了“吃糠咽菜”的苦日子。那时候后山区偏远农村的家常便饭仍是以粗粮(玉米、红薯、豆类等)为主,除了来客或串亲戚之外,很少见到“细粮”(小麦)。早钣多为吃得絮烦,喝得反胃的玉秫面或红薯面玉秫面两搅掺的咸面圪塔;中饭多为早已吃伤的玉秫糁儿熬成的,稠稠的,粘粘的玉秫糁儿饭;晚饭下些玉米糁儿,或和些玉米面水儿,加些黄菜(酸菜)、干豆角做成的“菜中饭”,也叫“调哩汤”。生活条件好的,擀几根杂面(豆、红薯干儿或小麦掺在一起磨成的面)条儿,下到锅里被称之为“糊涂饭”,已经是相当奢侈了。
说实话,这样的家常便饭真以难以下咽。你别撇嘴,不是我作孽,而是从小就是吃着这种饭长大的,上顿玉秫面,下顿玉秫糁儿,蒸的,烙的都是玉秫面馍,吃得够够的,腻腻的,絮絮的,早已与玉米结下了“不解之仇”,提起来就恨,就害怕哈。
只有来了客人,这种家常饭就端不出来了,得改改样儿,用白面拌面圪塔,擀面条儿,甚至割肉、煎鸡蛋来招待客人,所以叫“改样儿饭”,或“待客饭”哈。
郭汉老师有的是熟人,有的是办法。他说,寻饭吃想吃好饭也得有窍门儿,要么早点儿,要么晚点儿,不要赶到正吃饭时登门。正吃饭时候你去了,现做来不及了,人家吃着你看着,也不好看,不礼貌,只好将现成的家常便饭端出来,想吃不想吃,好歹也得忍着吃下。只有提前去,人家才有时间给你做“改样饭”;或者饭后去,人家饭吃完了,只好搁锅重新给你做好吃的。哈哈,蹭饭吃也有学问啊。
俺们托郭汉老师的福,沾他的光,基本上天天都能吃到“改样儿饭”。能喝上喷喷香的鸡蛋花儿白面圪塔;能吃上刚从鏊子上挑下来,又热又软,转着旋儿,起着层儿的热油馍;能吃上打着荷包鸡蛋,白生生,细拧拧,筋道道的“捞面条”;再不然拽一碗热腾腾,扯连不断的“鳖糊”面(烩面);或者是擀一碗薄闪闪,软绵绵,漂着小磨油珠的“宽面叶儿”(北冶骆岭一带称为“懒搽馍”)。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很有“嘴福”?
又有人不明白,吃的“改样儿饭”是不赖,睡“安乐窝儿”又是咋回事儿?我给你解释。
那个时候,农村的家里都很穷啊。我们当时在北冶后山说书的时候,家家屋里摆设寒酸简陋,没几样家具,就拿睡觉的床来说吧,大都是老式木床上面摆一张荆席(用荆条编成的席),再放一张苇席,就可以睡人了,极少有铺褥子、毯子、毛毡、单子的,我们乡下人称为“溜光席儿”,不是不想铺,而是铺不起啊。夏天睡上虽然硬梆梆地硌得身子疼,但冰凉透骨,倒也凉爽舒适;冬天就不好么好受了,又硬又冰,睡到半夜都暖不热席子,你说冷不冷?庄稼人啥都缺,唯一不缺是秸秆。每年谷子收割后,把秸秆晒干,收集起来整理好存放,我们乡下人称为“秆草”,是天然的免费褥子,往荆席上一摊,上面放上席子,软软和和的,可谓高级床铺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农村人都是睡“溜光席儿”。有两处地方不是“溜光席儿”:洞房,闺房。刚结婚娶的新媳妇儿,不但房间布置豪华,喜庆,就连床铺也上档次,绝不会“溜光席”,最起码也要铺上好看的大红毯子,大花单子吧?除了洞房,就数大闺女的“闺房”了。民间有“穷有小子富养女”的说法,再穷不能穷闺女。女娃们儿家穷不起,好讲究,爱打扮,当然不会象一般农村人那样睡“溜光席”,最起码也要在席上铺一条单子吧,相比普通床铺就上了一个档次。所以说,在乡下农村,大闺女屋,新媳妇房大都摆些花,挂些画,洒些香水啦,充满干净、温馨、舒适的气氛,被称为“安乐窝儿”
说到这,又有人撇嘴了,怎么,你说书的还睡过这“安乐窝儿”?不是吹哩,你别说,说书的还真睡过大闺女的床,钻过新媳妇的被窝哈!呵呵,越说越不照脸儿啦。喷得不着边际了,喷着喷着,喷掉地下了,拾起来吹吹重喷,都没想想,说书的真敢办这事儿,还能说(书)到现在不能?人家早把你们的腿给打断了,变成一群瞎子、瘸子啦!
别急,慢慢给你说。这真有这事儿,不过我没交待清楚,你们也想歪啦。灯不点不亮,话不说不透。那天,我们到后骆岭村,落脚到郭汉老师熟得不能再熟,关系铁得不能再铁的一户人家。主家招待我们吃罢饭,晚上住处发了愁。大村閁人口拥挤,地方都比较紧窄。人来客去,添个人口啥的,吃饭倒没啥,多添一碗水的不是,住宿是大问题,尤其冷天时候,家中往往没有多余的床铺和被褥,让人作难。男主家一咬牙,一狠心,给老婆商量说:“咱闺女去她舅家了,也没在家,就让他们住咱闺女那屋,睡她那床上吧?反正汉儿也不是外人。”女主家呢,也是个明白人,很痛快地答应下来:“咋不中?出门人难。天黑了,叫人家往哪去?好店只一宿。”就这样,我们算不算睡过大闺女的床呢?郭汉老师睡到床上,还说卖能话哩:“嗯,大闺女的床睡着就舒服。”
第二天我们就下涧沟了,涧沟分上、中、下三个自然村,系三个生产队,每个队说(书)两天,到上涧沟时,队长本不愿说(书),原因是钱没地方出,饭难派,没人支应,架不住郭汉是老熟人,抹不开面子。一狠心就不再求爷爷告奶奶地往下派饭了,吃住就在自己家。老婆埋怨:“吃饭我情愿管,晚上住哪哩?”队长挥挥手:“这还不好办?娃子干活没在家,新媳妇住娘家了,他们那屋、那床不是闲着哩?叫说书的就睡他们那床上!”掌柜说出来了,老婆也没法再说啥,只得去收拾屋子。哈哈,你说算不算钻过新媳妇的被窝?这是经人家同意,光明正大的,不是偷着摸着的,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龌龊哈。
有人想不明白,新媳妇的床铺能让说书人睡?真是不可思议。一来充分体现了我们新安县大山以下乡风之淳朴,乡情之厚道;二来还有一种迷信的说法,新媳妇的床让说书、唱戏、吹响器的人睡上可以驱邪、避邪。
看到这里,有人吓了一跳,又松了一口气。话不说透还以为俺说书的不是啥好人,不正派,不正气,耍流氓呢。看把俺们想成啥人了?说书人在三教九流里好歹也属于上九流,被尊为“说书先生”哩,咋会办那种下三滥的事儿?
涧沟说罢书,就南上望古垛了。
望古垛,平时人们念转音叫 “瓦骨朵儿”。“望古垛”三个字是生产队说书打条子时才知道这样写的。说起望古垛的由来,竟和初唐四杰之一,唐代大诗人,《咏鹅》的作者骆宾王有关呢,说起来还有一段悲壮凄美的传说故事。
骆宾王因当初帮徐敬业讨伐过武则天,武后登基就下令捉拿他。骆宾王并没逃往遥远的南方,而是出洛阳一路向西北,躲避在天子腋下。骆宾王翻过邙山,淌过畛水,顺着畛河的一条支流一直向上,来到了北冶附近。途经王坡沟时,遇山洪,不幸将其弱子冲走。宾王站在一山岭上,眼泪巴巴地望着幼儿漂流而去,伫望良久,故此地得名“望(子)古垛”。孩子的尸体搁浅在下游一沙滩上,故有“滩子沟”之地名。宾王怀抱死去的幼子,埋葬在一向阳山坡,此地得名“舍(子)坡头”,后来音念转了,叫“石坡头”。骆宾王住过的地方就是今天的骆岭村。老年丧子的骆宾王以后一直隐居在漏明,即现在的漏明河。
一个骆宾王的传说,引出了滩子沟、骆岭、石坡头、望古垛等地名的由来。初听这个故事,悲伤、感叹得一塌糊涂,真个是“看闲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啊,同时也长了不少见识,多了些向人炫耀的资本。
望古垛是个大村,有六个生产队。郭汉老师不止一次地说过,大村閁的书不好说。之所以不好说,主要是不好联系。这么多生产队集中在一起,找哪个生产队长呢?农村有句俗语“三人四靠,倒了锅灶。”找这个队长,队长会推托:“这两天老忙,先叫那个队先说(书)吧,俺们搁后面说(书)。”再换个队长,也是这套话。万事头难开,大家都不想当这个出头雁,领头羊,弄得说书的好像黄香膏药似的,谁也怕粘住甩不离了。你推给我,我推给他,像踢皮球一样来回踢。就好比蛤蟆吞西瓜,无从下口啊。还不比一个村就一个生产队,想推辞也没地方推。可是大村閁一旦(书)说开,就不止十天半月。
如此一块大蛋糕,岂能放过不吃?郭汉老师有的是办法,有的是活动能力。他不直接去找队长,而是去找“牌官儿”。
所谓“牌官儿”,就是当地爱揽闲事儿,爱出头,爱跑腿,有一副热心肠、责任心,且有一定的威望,在村中有绝对的话语权,说一不二的管事人。也称“排管儿”或“派管儿”。“牌官儿”不是队长,也不是村干部,啥官儿也不是,但是做出来的事儿能获得大家伙儿的认可和支持,说出来的话队长也得掂量三分。虽然不是顶头上司,但能拿捏住队长。所以说,在有些大村閁说书,找当地有影响力的“牌官儿”,远比找队长吃得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郭汉老师人太熟,对附近哪个村谁是有头脸儿的,爱听说书的,能办成事的“吃劲儿[②]”人都摸得一清二楚,了如指掌。当我们到了望古垛村口,准备打听队长在哪住的时候,郭汉把烟头一扔:“这样大的村,找队长中球用!推来推去推黄啦。走,上牌官儿家去”
郭汉老师所说的“牌官儿”在望古垛的村东头,很好摸,稍一打听就摸到了门上。郭老师轻车熟路般,径直摸进了院子,一边往里进,一边喊:“某某(名字忘了)哥,寻你来啦。很快出来一个老头,把我们迎进了屋子。
我有点怀疑,又装作不经意地打量一下老头,这就是郭汉老师所说的“牌官儿”吗,有没有搞错?在我的想象里,能在村子里踩一脚乱动弹,说出话都得听的“牌官儿”一定是气势不凡,威武霸气的风云人物。显然,这个老头距我的想象相去甚远。看样子六十多岁了,黝黑的脸,疑似粘附着灰尘乱蓬蓬的短发,略显驼背,走路一条腿好像一跛一跛的,穿一件没外套的黑棉袄,扣子不全,用一根布条儿勒着,从上到下,显得土里土气的。对郭汉老师找这样的一个“牌官儿”,说实话,有点失望和泄气。凭这个老头能办成事吗?
老头招呼我们坐下,推开了递到面前的“花城”,开门见山:“想来这村说书哩不是?”郭汉老师笑着说:“老哥,卖啥吆喝啥,吃啥粮叫唤啥声儿。来这儿啦,不说书咱会干啥?中间无人事不成,想求老哥帮个忙,跑个腿儿,搭句腔。知道这事儿离了老哥不中,给你添麻烦来了。”
郭汉老师一口一个“老哥”,老哥长,老哥短的,听着亲热得肉麻。老头不多搭话,站起身说:“你们在家等着,叫我去找队长,再晚出去了,就逮不着人啦。”
郭汉也站起来:“老哥,叫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老头瞥了一眼:“你去会弄啥?看不见,还得叫我给你领路?”
“要不,叫俺徒弟这个明眼儿去,啥样?”
老头摆摆手:“不用,你们在家歇着老等,晌午就在这吃饭。”交待完就一颠一颠地走了出去。
老头走后,就剩我们三个陌生人呆在他的家里。屋里呆得无聊,出来透气,闲看。院子不大,出了正房,下了两三个台阶,两边就是两对厦的厢房,厦房都不大,东上首是厨房,下首却是杂物间和牛屋。西边则是住室和盛粮的仓库,中间的院落成了一个狭长的过道,临近大门处还吊了满满的一大架玉秫秫棒子,使整个院子看起来更窄,更拥挤。从院子到屋里的摆设来看,老头的家境并不富裕,甚至是清贫。趁家中无人,我和王河清老师问郭汉老师:“这老头家里好像人口不大?”郭汉老师想了想:“嗯,老伴已经去世了,大概一个儿子,两个闺女吧。儿子成家另立门户,大闺女已经出门了,二闺女应该没出门吧?今早也没见着在家。”
正说着,大门“吱吜”一下开了,进来一个姑娘,冲我们腼腆的一笑,直接进了厨房。不用说,肯定就是郭汉老师所说的老头家二姑娘了。两位老师看不见,虽然我能看见,但一个年轻姑娘家,人家没搭腔说话,也不好意思主动开口打招呼,怕引起难堪。
中午,老头回来了。我赶紧站起来问候:“回来啦,爷们?”。老头点点头,径直冲郭汉说:“事办成了,六个队,一个队三天,已经挨置好了,总共十八天。都是我支应,照护(顾),吃住也在我这。”
老头仍然话不多,一付邋遢的样子,但不得不让人另眼相看。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么大一个村,这么多生产队却让一个貌不起眼,少言寡语的老头轻松搞定,简直不可思议!郭汉、王河清两位老师叹服之余,连连表示感激之情。
事儿已说成,但媒人不能替新媳妇上骄。十八天书能不能顺顺当当地拿下来,主要还得靠说书人自己。书是否过,演出能否打响、叫好儿,让观众满意和喜欢。如果书打不响,大家不欢迎,“牌官儿”再能办事,再强硬也是枉然,也许三天两天,也许一天半天就会收拾“卷铺盖离庙”。事到那种地步,别说说书人灰头土脸,狼狈尴尬,就连“牌官儿”也弄得没有面子,下不来台,都不好看哈。
不过这种担心纯属多余,王河清老师的书说得不是一般的“硬扎”,唱一处,响一处,据我知道,从来没有打“窝杆[③]”过,此次亦然。王河清老师的《刘镛下南京》一炮走红,赢来满场喝彩。为我们打响了牌子,为“牌官儿”争足了面子。当他说到大街上旋风拦骄告状的“旋风案”时,已经把听众牢牢地拽住了。再往后的“九头案”,把接而连三的九个人头都挂在桥杆上时,听书的已经走火入魔,欲罢不能了。这时候即使有队长想反悔也不行,下面听众不依啊。
说书进展得很顺利,这个队说罢换那个队,按班就绪。晚上说书,白天两位老师忙着算卦拾“外块儿”。我呢,就借背词儿、练腔之名,到处闲逛,瞎转悠,倒也逍遥自在,其乐融融的。
我们吃住都在“牌官儿”家里,给人家添了不少麻烦,很感到过意不去。但老头父女俩没有一点儿厌烦的表示,让人不仅感叹,出门在外,还是好人多啊。
清晨,两个老师还是睡梦中,我就被外面一阵阵“呼呼呼,嗡嗡嗡”似机器轰鸣之声唤醒,便没了睡意,穿衣起床,好奇地着急跑到外面看看是什么声音。
到外边一看,哪来的机器轰鸣之声?原来是门前石磨发出的声音。一台石磨不可能声音那么大,能把人吵醒吧?发现上下左右的邻居家门前的石磨都在转,往远处听,村中比比皆是石磨之声。
那个时候,后山一带还没有通上电,就谈不上机械化,当然也没有当时农村人羡慕的“钢磨”,不管是“一风催”,还是“遍遍净”,庄稼人都叫它“钢磨”。乡下人吃的白面、玉秫面、红薯面、玉秫糁等都要靠石磨来完成,成为家家必备的工具。石磨相对来说是比较原始、落后的,效率很低。磨一升子面,推的推,拉的拉,磨的磨,箩的箩,几乎得一晌子忙活。粗粮营养不高,利用率低,加之农活体力劳动强度大,庄稼人往往饥得快,吃得多。普遍饭量都大,消耗“粮饭[④]”也快。一升面遇到人口较多的家庭,也只能支撑一两天的光景。所以,那个年代家家门前的石磨几乎是天天都不能闲着。
一时来了兴趣,顺岭头漫步西行,往南可以俯瞰整个村子。几乎每家的门前都安上石磨,几乎每盘石磨都在“唿唿唿”地转,都在“轰轰轰”地响。有两个人一边一个手工推磨的,也有一个人单挑独干,费力地推动石磨转动的,但绝大多数是套上牛来代替人工。牛推磨都是戴着“掩眼[⑤]”,或用破布将眼蒙上,套上笼嘴,将磨杆儿直接搭在牛领上,由牛拱着前行。牛为啥要蒙眼和戴笼嘴?戴笼嘴是有效防止有的牛吃嘴,偷吃磨盘上的粮食。蒙牛眼据说可以避免牛长时间绕着磨子转圈而引起的眩晕。还是一种说法,牛是有灵性的,它看到辛辛苦苦磨出来的粮食,被主人剥夺,自己却吃不到,心里容易不平衡,一闹情绪就不好好拉磨。干脆把眼蒙上,不让它看到,眼不见心不乱,就能踏踏实实地干活了。
石磨上的粮食五花八门,有拉玉秫糁儿的,有磨玉秫面的,有磨红薯面的,有磨豆面的,当然,也有磨白面的。石磨旁不是安一个箩面缸,就是支一个箩面簸箩,上放“箩面窗儿”,粗箩、细箩,纲丝底儿,尼龙底儿,形形色色,各种各样。
一家家,一盘盘转动着的石磨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无数石磨发出的声音合奏出一曲气势恢弘的交响乐。箩面声、喝牛声、说笑声则成为这曲交响曲中欢快跳跃的音符。而风暴线,交响乐则交织而成一幅幅有形、有声、有色的动态画面。
行走在风景线上,置身于动态画间,陶醉在农家乐里,倍感震撼、愉悦,流连忘返。忽然发现太阳不知什么时候从邙山那边偷偷爬了出来,升起了一竿子高,笑迷迷地朝这边望。这才想起,不早了,老师们应该起来了,该回去吃早饭啦。
等我回去时,老师们已经起床洗漱完毕,坐在上房屋的客厅里了。朝厨房瞄了一眼,见老头的女儿好像已经烧好了玉秫糁汤,炒好菜,把摊馍鏊搁火上正在摊“摊馍”。

摊馍用的“摊馍鏊”
摊馍是当时新安县大山以下很普遍的一种美食,有专用的工具叫“摊馍鏊儿”。“摊馍鏊儿”是一种特殊的鏊子,呈圆形,分盖和底座上下两部分。盛摊馍的底座系中间薄且向上拱起、四周有凹槽的一种铁制鏊子,最下面有三条腿儿支撑。整个形状看起来有点象古装中的官帽儿。用“摊馍鏊儿”烙出来馍叫“摊馍”,把做摊馍的过程叫摊“摊馍”。又因为“摊馍”是一次性摊成的,不象烙馍那样来回翻动,所以有些地方也叫“不翻儿”。

新安县农村的“摊馍”
那时候人穷,生活水平低,“摊馍”多用玉米面、红薯面,或是两搅掺的,极少掺入白面的。小米面摊 “摊馍”最佳,最好吃,但不是家家吃得起,人人都能吃的,偶尔吃一次,无疑于珍宝佳肴。
厨房里“摊馍”的香味已经飘了出来,钻到了郭汉老师的鼻子里。可能有些饥了,阵阵馍香勾起了他的馋虫,有点等不及了,就催我:“武成,学勤快点,别坐着等吃等喝,去厨房给人家搭把手,做快些。”
我没有说啥,坐着也没有动。对郭汉老师指手画脚地乱支使、派活儿,颇有些不以为然。做饭就是人家女人们的事儿,最忌讳男人们到厨房胡乱搅和,弄不好会惹人反感和讨厌的。尤其是彼此之间不是太熟识,不托底细的,冒然打扰,反而适得其反,弄巧成拙。何况人家是一个大姑娘家的,你一个大小伙子的钻进厨房帮忙,算怎么回事儿?难免让人多想。唉,郭汉老师真是的,怎么不知道啥叫避嫌呢?就知道瞎指戳。有心怼他一句,说得恁美,你咋不去帮忙哩!想想算了,徒弟怎么敢轻易冒犯师傅呢?老师永远正确哈。
不一会儿,姑娘已经端着两碗汤进来了。我慌忙收拾桌子,又赶紧站起来将接过,置于桌上,这是礼貌。郭汉老师又开始发号施令了:“武成,恁没眼色,坐这硬等着叫人家端吃端喝哩?还不赶紧自己去端!”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一边答应,一边赶紧往厨房跑,想想郭汉老师训得不无道理。自己就是有点迟钝,没颜色,手脚不勤快哈。三个大老爷们坐着,让一个小姑娘家端吃端喝的,确实不太好看。于是就争先恐后地跑到厨房,一手端起一碗汤,另一只手去拿馍,发现摊出来只有六个,就一并拿到上房屋放到桌子上,招呼两位老师先吃。
干吗让两位老师先吃,自己不吃?刚才进厨房一看,就明白了。姑娘家到底年轻,做饭经验少。摊馍虽好吃,但不经吃,不耐吃。能吃黑窝头,不吃稀贡稠。意思摊馍是稀面糊熟后变成稠的,吃得费,吃得多,吃后还不耐饥,没有黑面馍吃着止饥。同是一个人的饭量,就比其它馍吃得多。摊馍是一个一个地摊,做起来比较慢,耽误时间。人多场合现摊现吃,根本就跟不上事儿。类此情况,姑娘应该提前摊好足够的数量,开饭时才不致紧张,供不应求。显然开饭有点早了,三个人六个摊馍远远不够吃的,等吃完了,摊馍还摊不出来,就有点尴尬了。为了避免桌子上的摊馍“断供”,只好让两位老师先吃,自己再等等吧。
两位老师看不见,也不知道摊出来的摊馍够不够吃,自顾津津有味,香喷喷地狼吞虎咽,丝毫没发觉他们的徒弟既没动手,也没动口,眼巴巴地瞅着他们往嘴里送。唉,从小老母亲就交待过我,不管是串亲戚,还是待客,要记着,吃饭是往眼里吃的,可不是光往肚里吃的。当时不懂,感到好笑,明明是往嘴里吃的,偏说往眼里吃的,眼会能吃东西?长大后才明白是咋着一回事儿。呵呵,人家两位老师没有眼,不用顾忌那么多,只管往嘴里吃了。谁叫咱倒霉,生了两个黑窟窿眼,吃东西就得看眼色行事哈。
很快,六个摊馍风卷残云般地没有了。郭汉老师伸手在盘子上摸不到摊馍,又抹了抹嘴,命令我:“武成,馈捞儿。”
“馈捞儿”是江湖说书行的春点儿,外界称为“黑话”,意即外人听不懂的话。“馈”是“拿、取”之意,“捞儿”是指“馍”。意思就是让我去厨房拿馍。我只好回答:“念了,没造奸哩。”意思就是:没有了,馍还没摊出来呢。两位老师恍然大悟,王河清老师笑着调侃:“汉儿,咱俩老没成色,武成还没动筷子呢,六个馍叫你我可报销完啦。”郭汉老师也不好意思地笑着:“不是是球!谁叫咱昭不见哩?
说笑间,又摊熟几个馍送了进来,终于解围。
不知不觉,半月过去了。说书轮到最后一个队时,出现点小插曲。六队队长小名叫“猪娃”。过去父母待小孩儿娇,往往会给孩子起一些鸡、狗、猪等小动物的名字。迷信说法,名字越丑,越难听,越能长命百岁。轮到六队时,队长猪娃说,队里没有现钱,托“牌官儿”问问,看能不能赊账。郭汉老师犹豫了一下,就回话,赊就赊吧,都是老熟人啦,又不是跑户,迟点晚点给钱都没事儿。于时,十八天说书顺利杀青。
事实证明,说书赊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和后遗症。此后跑了两次,钱都没要到手。直到临近年关,刘八岭说书结束后专程又赶到望古垛,三个人住在那里等了三天,才把钱逼到手。外人问起,郭汉老师开玩笑道:“俺们来要猪娃账啦!”此是后话。
[①] 不好事:河洛方言,不多事,不爱搬弄是非。
[②] 吃劲儿:河洛方言,能使上劲儿,办成事之意。
[③] 窝杆:新安方言,原意是打猎枪时,枪籽儿窝在枪杆儿里面出不来,称为“窝杆”,“打不出”,多引申为做事不成功,失败。
[④] 粮饭:新安县大山以下的土话,把米、面和食品统称为“粮饭”。
[⑤] 掩眼:用草或布条旧麻绳之类编织而成的半球形,蒙在牛的眼上。称为“掩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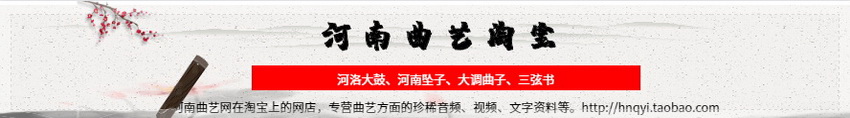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