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廿四

回家停了几天,稍作整顿,再过河北时,已经不需要坐船,因为黄河吊桥已经刚刚建成通车。一桥飞架南北,顶替了多少渡船。我们从仓头沿畛河北下,至狂口,见渡船而不坐,直奔黄河吊桥。一来可以省去两块船钱,二来可以见识并体验一下走黄河索道桥的感觉,想想都兴奋,何乐而不为?

黄河吊桥,也称黄河索道桥,位于狂口与西沃之间的南石崖下,距狂口不过四五里路,很快就到了。所谓吊桥,就是没有一个桥墩,整个桥都是悬空吊在黄河上的。吊起大桥用的绳子是六十四根比鸡蛋还粗的钢丝绳排列起来,两头分别拴在两岸用水泥浇筑的铁桩上。据说这是备战桥,在战时可以二十分钟拆除,也可以二十分钟重新搭建成功。人们传得神乎其神,说这座桥分分钟可以缩进桥南石山的石洞里。为此,我还特意扒着桥南头的石洞口瞅了瞅,除了一排排的钢丝绳外,黑咕咙咚的,啥也看不清。
我们过桥这天,恰巧刮着响西风,走在木板铺就的桥面上,明显地感受到吊桥在左右摇摆和上下抖动,有一种飘起来的感觉,战战兢兢走到一半时,有点像驾云,好怯啊,又不能拐回去,只好硬着头皮跑过了桥。
甩掉了王矿子这个包袱,我们确实轻松了不少。赶起路来没有前拉着后推着的磕拌,速度也快了不少。走西岭,下下冶,翻石槽,越逢石,一路顺风,一直征北,真奔王屋。
有的说,你俩不是出门说书,是出来“溜腿儿”哩。兔子才“溜腿儿”的这不骂人的吗?咋光跑路,不说书呢?当然是一路联系着说书,哪饥哪吃饭,哪黑哪住店,有书就说书,没书就赶路,一边说着书,一边奔那个方向去的。只不过都是些说书的日常,没有啥特殊的,值得提及的事儿,被我省略罢了。你没听说书的常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吗?
通过两个多月的磨合,我和刘大江配合得更默契,合作得更愉快,相处得更融洽,书场上更成功。他常说的《双锁柜》《移胎案》《宋仁宗私访陈州》我基本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越来越熟练,越来越得心应手。我利用文学方面的一点小优势,对刘大江说的书更进一步的加工,细化,精以求精,使其更加接近完美。这不是吹的,经过我再加工、润色的书,连刘大江也赞成,服服帖帖地采纳。
我们两个轮换着,一人一板地说(书)。刘大江再也不是以前的一人一台戏,一人一场书,一唱到底不歇气的“一言堂”啦。有我抵挡了一半,使他省力了不少,为此还不止一次地表示感激我,分担了他的负担。我呢,得益于人家的强硬“逼迫”,徐徐引导,从生涩走向成熟,从毛手毛脚走向沉稳,终于完成了由唱小段到说大书的成功转型。正如《十五的月亮》里唱的,我说书成功的军功章里,有王新章老师的一半,也有刘大江老师的一半哈。我有什么理由不感谢人家?
刘大江鼓励我:“不要光拣我会的书说,你会有啥大书,也得拿出来亮亮呀。”
我说:“听得遍数最多的就是俺老师的《彩楼记》,已经记得差不多了,也不知敢说不敢。”
“咋不敢,学会的东西窝在肚子里,不往外出,等着在肚子里沤烂哩,还是在肚子里下娃儿哩?”
“我怕拿不下来呀。再说我一个人说一场书,顶不到底啊。”
“没事儿,说吧,这不还我有嘛。我给你兜底儿,还怕啥?”
听他这么一说,我便有了底气,于是在石槽大队的一场演出中,由我开大书《彩楼记》,因为事先做过充分的备课,所以进展一切顺利。一口气说了三大关(三大段)书:第一回,抛彩(球);第二回,借银(盘缠);第三回,别相(父女闹别扭)。从学艺到现在,哪出个这力呀,累得我头晕眼花,喉咙又干又疼,想哑了的样子,大有罢工之势。搁黄河南,三板书就结束了。黄河北不行啊,听众不干,赖着不走,非要让再说一关不可。大家想听是好事儿,说明书“入馈”啦。可我实在说不动呀,便悄悄求救:“刘先儿,赶紧救急吧,嗓子受不了啦。”
刘大江笑笑:“这有何难?你把情节给我介绍几句。”
我附耳给他简要地介绍了几句,大致就是:刘瑞莲小姐和父亲刘丞相吵了一架,大闹了一场后,一气之下,哭着跑离相府。丫环奉太太之命追赶送银,又被小姐赌气撕了包裹,纹银散了一地,哭回寒窑(她和吕蒙正居住的地方)。来到洛河边上,又寻思,没有借到盘费,无颜面再见丈夫,便扯乱青丝(头发),长袖遮面,就要投河自尽。“书扣儿[①]”设下,就可以刹书了。
刘大江胸有成竹地点点头,掂起板就开始了。到底是经过“战口”的说家儿,唱得不慌不忙,说得稳稳当当,一切按我交待的情节有条不紊地进行。除了把原来的“天仙韵”变成好唱的“丁咚韵”之外,从唱词到道白,从人物塑造到情节结构,几乎无可挑剔,最后完美收官。
自此,我们的合作又多了一部大书《彩楼记》。
我们配合得最默契,合作得最完美,演绎得最精致的当属《双锁柜》。熟练后不仅我们可以一人一关轮换着说,而且绝大部分内容,都可以分角色说“对口”书,且对得风雨不透,滴水不漏。不但唱起来省力、省心,出来的效果还不是一般的好。书场气氛活跃,听众兴致盎然,乐此不疲。
尤其是其中“请神坐坛”一节儿,是《双锁柜》中的重头戏,让我们简直把假的演成了真的,让听众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欲罢不能。
早在前面“神书还愿”一章说过,我的母亲请神、敬神、坐坛一辈子。虽然我不信,有时被骂得体无完肤,但毕竟从小在此环境下长大,耳熏目染,不知不觉中学会了不少。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咋走哩,没请过神,但见得多呀!哎哟,打嘴,这个比喻不老恰当。
“请神坐坛”是《双锁柜》书上的说法,在我们那里不叫“坐坛”,叫“坐堂”。还有个不太文雅好听的名字,叫“下神”,取“神下来附体”之意。“下神”是人们背后的叫法,当着“神”的面不能这样叫。只有猪下娃儿,驴下驹儿,鸡下蛋,怎么能说是下神呢?有点大不敬啊。
和刘大江相比,请神坐坛是我的强项。《双锁柜》请神这一段儿,内容和书词已经编得够精彩了,刘大江已经把这个情节演得够活,够逼真了。但从我接近专业的角度来审视,还达不到十全十美,和真实的请神坐坛比起来,还是有点不太像,有点那么不尽人意。这点儿刘大江得服气我,也得听我的,就把“坐坛”的“主角儿”让给我,自己甘愿“绿叶配红花”。
我先是请神的“主角儿”——余蒲姐的二姨,老康氏的妹子,著名的“神婆”康二妮。开始烧香念经,让刘大江做“配角儿”——余蒲姐的妈,老康氏,作陪跪状,附和着“打佛儿[②]”。等经念得差不多了,神该下来啦,我开始转换角色,摇身一变,由请神的成了坐坛的,于是,“神”桃花姑姑下凡,附着在康二妮身上。即我被“神”附体,成为桃花姑姑的代言人。
我一本正经地装神弄鬼,刘大江“恭心诚意”地请神问神,把以假乱真做到了极致。倾倒了书场里听书的几个烧香念经的资深神婆,佩服得五体投地。任我如何解释,这是演戏的,不是真的,仍固执地认为我就是专业的,门内出身的“神汉”,相关领域的“专家”。非要邀请参与请神活动,给他们坐一坛,让大家领教学习一番。吓得我赶紧连连推辞,躲得远远的。咱这两下哪敢鲁班面前耍斧?被看出破绽,露出马脚,岂不是秆草夹老头——丢个大人?
在邵原街说了几天书,听说离山西阳城已经不远了,便萌生了去阳城说书的念头。
在黄河南想去河北,在黄河北想去阳城。只所以想去阳城,是对那边的风情民俗充满好奇:
一是早就有“阳城闺女晋城小”的说法,意思是阳城的水色好,出落的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晋城的水土好,出来的小伙一个比一个英俊。还有一种解释是,阳城的闺女多,晋城的小伙儿多。如果说河北的闺女貌如花,则阳城的姑娘美如画。出于那个年龄嘛,听说哪个地方大闺女多,姑娘长得排场,就如磁铁般地产生一股吸引力,想去见识见识,幻想着万一能呱哒[③]一个回来呢?
二是听说阳城有“睡大炕”的习俗,且传得神乎其神。何谓“睡大炕”?据说是山西阳城的大山里冬天很冷,盛行盘大火炕,火炕下面设火道与厨房的灶台相通。烧火既可以做饭,也可以给炕供暖,一举两得。又听说,不论是一家人,还是亲戚朋友,还是远道而来的客人,统统挤在一个炕上。又听说,炕很大,正中间放一张小桌,有的说是火盆。吃饭时所有人都盘腿坐在炕上,围在一圈儿吃饭、喝酒,或烤火、聊天。又听说,睡觉时所有人头朝外,脚朝内环桌(或火盆)而眠。
有的问,男男女女混在一处睡,不分老公公儿媳妇,女婿和老太人,怎么可能?这不乱套啦!自家人吧,还勉强说得过去,你说一个外来的陌生人也挤在一个炕上,打死我也不相信!咋说呢?一地一个风俗,一处一个规矩。可能人家当地就是那种习俗,见怪不怪罢了。
有的又问,外地的陌生人,不知根知底的,男女混杂,出点啥事儿咋办?你能想到的,人家都替你考虑好啦。据传说,虽然是男女一起睡的,但一人一个被筒儿,尤其是外人,还是设防的。男女中间竖一块砖头。夜里不管咋动弹,咋翻身,不能把砖头给弄倒了。第二天早上,主家如果发现砖头倒了,二话不说,没吃饭以前,先舀上一飘冷水,让你当面喝下。如果不肯喝,说明心里有鬼,害怕喝了得阴症活不成,这事儿不能到底;如果痛痛快快喝了,并且没一点事儿,说明是不小心误把砖撞倒的,一切烟消云散。
有人好奇,你说这事儿真的还是假的?你问我,我问谁去?反正我也是听别人哈哧[④]哩,没有亲眼见,也是半信半疑哈。要不怎么急着亲自去阳城探个究竟呢?
刘大江也没去过阳城,但他说了一个有关说书人在阳城的趣事儿,而且说得还是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儿的,不可全信,但不能一点也不信:
他说,有一个说书的,到阳城的大山里说书。大山里人烟稀少,几十里山路一户人家。夜晚说书,听书的来自方圆几十里路。那地方冬天闲时,男人们都出去干活了(那时候还没“打工”这个词儿),家里边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姑娘媳妇。老弱病残的跑不了远路,也听不成说书,来听说书的都是大闺女小媳妇。为啥是小媳妇呢?就不能是大媳妇,老媳妇?你想,年经稍大点的媳妇夜里都得奶孩子哩,也出不了门呀;只有刚结罢婚,还没生小孩,没有累赘的新媳妇,小媳妇才能出得门哈。听罢书夜里太晚,就不走了,和说书人挤到一个炕上睡。大屋中间放一个所有人共用的尿盆。夜里说书人被尿憋醒了,有心起来尿尿,四周都是女的,感觉老难为情。刚一动弹,便有姑娘立即把炕桌上的灯点着,说:“说书先儿想尿哩,赶紧起来吧。”说书人见点着灯亮堂堂的,越发不好意思起来了,连忙说:“不尿,不尿。”如此反复几次,憋得真是受不了啦,只得爬起来,站到尿盆前,在姑娘媳妇们众目睽睽之下,站了半天竟然没尿出来,只好又钻到被窝里,结果把膀胱憋出了毛病。第二天赶紧去住(医)院,吓得再也不敢去阳城说书了。
哈哈,是不是特搞笑?有人说,你这说书的说这事儿恐怕背着干粮,三天三夜也打听不着吧?说不准,反正我也没去背着干粮打听过。常言说,三里(一说“山里”)没真信儿,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是真是假,去阳城看看不就知道了?人都说,不到黄河心不死,这都过黄河啦,又该“不到阳城心不死”啦。
那还犹豫啥?去阳城!到那看看,大闺女究竟长得排场不排场,顺便体验一下“睡大炕”到底是啥感觉。
眼前边有书也不说了,说走就走!打听好路线,从邵原下山便是东阳河大峡谷。顺河逆行,过了些记不清名字的村落,无心欣赏沿河两岸的冬景,经黄楝树,至黄北角。越往后,村庄越小,住户越少。
天黑了,不能再赶路了,就在山上找到一个小村儿,人不多,大概十来户人家吧。找着队长,很容易就联系住书场。在这说(书)了两天,白天上山转转,冬天很萧条,没啥风景可看的。柿树不少,都是光秃秃的伫立在山风里,没有一点儿生气。随处可见野生的核桃树,树下落满一层早已风干的山核桃,顺手拾起一个,磕开,整个果仁儿能轻松的扣出来,放到口里,香得直咂巴嘴儿。山里人少,核桃太多,已经没人要了。有心捡些捎着,心有余而力不足。家家房山墙上挂满了柿饼,荆芭或竹箔上摊满了柿瓣儿。山里人厚道,热情。一碗捞面条儿里几乎有一半羊肉,我尝了尝,特好吃。刘大江精明,害怕吃不完,把羊肉拨到我碗里好多。我沾沾自喜,以为沾住光了。谁知吃到一半儿,说啥也吃不完,结果剩到碗里了,弄得很难堪,好在主家一点也没怪罪的意思。临走时,家家都端出来柿饼、柿瓣,让我们带着。真想拿啊,无奈行李太重,不利“行军”,只好婉言谢绝了人家的好意。好多年过去了,至今想起来,心里还暖暖,忘不了那些年,那个大山,那些仅相处两天却视我们如亲人的父老们。
我们打听了一下,到阳城地面还需要翻过一座大山,有三四十里地。大家常说:山里人不论理。其实不是这个“理”,而是路程长短的那个“里”。山里的四十里,你得打着五六十里路走。咋着哩?不是山里的“里”长,而是上山下岭路难走,费力,就感觉远了不少。
不管咋说,反正是离阳城越来越近了,隔一座大山,仿佛看到了山那边冉冉升起的炊烟,闻到了随风淡淡飘过的米香;仿佛听到了姑娘们银耳般的笑声,感觉到热呼呼的大炕在向我们招手。每想到此,精神陡增,上起山来腿不疼,腰不酸,面不改色气不喘,恨不得插翅飞往阳城。
想归想,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出来。如果你没走过阳城大山的路,就不能真正体会啥叫“羊肠小道”。由于人烟稀少,人迹罕至,山上的路很窄,很陡,很不明显。大部分的路被杂草荆棘所侵占,一边走,一边还得手脚并用,用手拨开荆棘,用脚踢开杂草,可真谓“披荆斩棘”哈。一边走,一边还得辨认方向,判断哪是上山路,哪是远行通往山那边的路。不然的话,走着走着,路就没了,还得回头再走。判断上山的路主要看路上的牛粪、羊粪多不多,如果路上撒满了羊屎蛋儿,不用问,肯定是上山的路,走不远,及时更改。说爬山路不累,不作难那是瞎话。如果不是提着劲儿,早就累趴下啦。唉,想看人家的大闺女,想睡人家的大炕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山路崎岖难行,走起来感到特别漫长。这不,快晌午啦,才走有十几里地。不说冷了,额头上还挂着细小的汗珠,衣服好像要溻湿的样子,折腾了一晌子,已经是“老饥变老渴”啦,嗓子想冒烟。要命的是,这十几里山路,没有见到一户人家,找口水喝都难。
就在我们饥渴难忍,几乎要绝望之时,又转过一个岭头,眼前豁然一亮,拐过弯儿的山洼里隐隐约约现出一处房子,有一溜极轻,极淡的青烟从那里荡出,随风飘过来一线炊香。哈哈,有房子,有烟火处,必有人家无疑!我们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又好像遇见了外星人,又好像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我们如瞬间吸食了一颗鸦片,打了一针兴奋剂一般,立即精神抖擞起来,脚步也不沉了,动作也加快了。紧走几步,便到了那房子跟前。
从外面打量,是一个简陋、陈旧的农家小院。没有大门,只用石块儿简单地垒了一段遮挡的残墙。三间上房和两边的厦房都是下边用石砌的尺把子高的根基,上面用土打就的夹板墙,历经风雨洗礼,早已斑斑驳驳地刻下了岁月的印痕,房顶上面晒的并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小瓦,而是就地取材,用一块块又薄,又大,又方,又齐整的石块儿铺就。院子里有一位看起来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正弯腰专心致志地往搁着蒸锅的简易柴禾灶中送柴,炊烟就是从这里飘出。
我们还未及仔细打量,院里就有一条黄白相间的狗汪汪地叫着迎了出来。不过,看到我们后,叫的语气很温和,一点儿也不凶恶,也没有扑过来要咬我们的意思。感觉就好像应付差事一般,习惯性地叫两声,告诉主人来人啦,就算完成自己的任务了。这畜生通人性,一边朝我们叫,一边回头看主人。直到老太太直起腰来,朝它轻轻地喝了一声,立即撒回,摇着尾巴退到院内,乖乖地卧到一边儿睡觉去了。
我恭恭敬敬上前,连说带比划地打招呼:“老大娘,我们是说书的,路过这里,想讨口水喝,你看可以吗?”
老太太打量了我们一下,缓缓地说:“挫偎。”我们听懂啦,河北把“坐”不念坐,念“挫”,“屋”不念屋,念“偎”。“挫偎”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进屋里坐。
我们又高兴又感激,本想坐在院里的石凳上喝口水就可以了。老太太又指了指上房屋:“挫卧。”“卧”是那,那里的意思。老太太真厚道,以为坐院里不是待客之道,把我们往屋里让。我们连忙点头哈腰表示感谢,跟着老太太进了上房。
乘老太太忙着烧水的空儿,打量一下房间。这三间房是通着的,中间没有隔扇,显得非常宽敞而又有些空荡荡的。正中间靠墙摆着一张桌,桌后面挂着神轴子,桌上安放香炉,纸箔等。看起来老太太是烧香敬神之人,怪不得爱做好事,善事呢。靠后山墙的东北角盘有一火炕,比床大,但没有传说中阳城的大炕大。说话不及,老太大端了两个冒着热气的黑瓷碗进来,我们忙不迭地站起,慌忙接过一看,呀,哪里是白开水,分明是鸡蛋茶!茶是热的,看着老太太温暖的眼神,我们心也是热的。茶还没喝完,老太太热腾腾的蒸馍也端了进来,又是端汤,又是盛菜。菜是山菲菜腌制的,味道长,特好吃。看来不用我们张嘴求告,今晌午这顿饭是混到口了。
一边吃着饭,一边尝试着和老太太扯起了家常。一搭腔说话,发现这里虽然离阳城很近,但说的仍然和济源话差不多,而济源话和河南话也很接近。所以我们之间谈话,大部分相互都能听懂。交谈中得知,老太太家中人口不大,老头已经不在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去外面干活了,跟前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儿,二儿子是哑巴,在家放羊拾柴禾。我们这才留神一下,炕上睡着一个小女孩儿。刘大江试探着问,闺女她妈呢?老太太淡淡地回答,她没有妈。怎么可能,没有妈,女儿从哪来?但我们都没敢往下问,估计是儿媳妇离婚跳起腿走了,只是猜测而已。
吃饱了,喝足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站起来,作离开状。老太太挽留道:“再走天黑也找不到落脚地儿,就在这说(书)一黑夜(促读(hèyē)吧。说神书,照掏钱儿。”
我们巴不得呢,就趁坡下驴就留了下来。天黑后,早早吃罢饭,老太太在神轴子前烧上香,口中念念有词一番,这里念的请神经和别处的大不相同,我们听了半天,也没听懂一句。
这是自我说书以来,听众最少的一次。两个人说书,三个人听——老婆、哑巴儿子和小孙女。尽管孙女才七八岁,不知说书是干啥的,但好歹也算是个听众吧。哑巴听不见,只能看我们嘴动弹,手比划,不能算听众,却成了名副其实的“观众”。
看到听众这样少,我有点儿存不住气,悄悄对刘大江说:“刘先儿,这没有‘听家儿’,提不住劲儿,咋说书哩?咱说给墙听哩?”
刘大江笑笑:“人多人少都得说(书)呀,挣人家的钱,吃人家的饭,就得好好给人家说书。没事儿,只当在一边儿锻炼哩,或者全当是背书哩,这样想着,书就能说好了。”
老太太也看出我有些犹豫,就说:“有人听没人听只管说,俺是给神说(书)的,不是给人说的。”说得也是,人越少,还越得搁劲儿,把书说好,不然怎么对得起这两顿饭钱,还有三块的(说)书钱?再者,还有“人在说,神在看” 呢,耍滑头,神不容啊。
这场书我们也无法论板儿啦,唱一段开始道白时,老太太就赶紧说:“不用慌,歇歇,天老冷,快来我(这)烤火。”我们就坐下来烤一会火,问老太太能听懂不能,老太太点点头:“能懂,好听。”歇一会儿自己感觉没意思了,就站起来说。如此说说停停,也分不清楚说几关书了。小孙女听不懂,坐一会儿,呵欠连天:“奶奶,我要睡觉觉。”就打发上炕睡了。
三个观众成了两个,一对一服务。又说了几段儿,老婆说:“慢慢说(书),我去做饭。”怎么夜里还吃饭?你打听打听,说书的到哪里没有夜餐?况且阳城一带自身就有吃夜饭的习惯。
这可倒好,两个人说书,一个哑巴在听,不,严格地说,是在看。我们知道,聋子耳朵是陪衬的,哑巴耳朵呢,是做样儿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得再好,声音再高,都是枉然,他也不会听见的。但是,人家还是一动也不动陪着我们,瞪着眼,张着嘴,装模作样地在听。我们呢,就尽量地多带动作,多比划,力争用手势、手语让哑巴尽可能地明白我们说的是什么。
第二天早上吃罢饭,我们告别老太太出门,抬头望天,阴沉沉、雾蒙蒙的。太阳不知是睡懒觉了,还是躲在云背后不肯出来。山风刺骨,令人打了个寒噤。啊,天要变了。腊月天变,肯定要下雪。老太太听说我们想去阳城,就劝说,你们没来过,没人领路,最好别去。几十里地,没有一户人家,山路不好走不说,错综复杂,叉道甚多,万一摸迷了路,连个问路的都找不到。天眼看要变,万一下大雪,把你们困在山里,进不去,出不来,前不沾村,后不着店,不冻死,也得饿死。
老太太一番话,拔掉了我们的气门芯儿,一下子泄了气。山里的路,昨天已经领教过了,青天白日,尚难以分辨路形,如果一场大雪覆盖,哪还会有路的影子?大腊月的,快过年了,为了贪图看大闺女,睡大炕,万一孤军深入,让大雪围追堵截,被困阳城,抽身不得,不能回家过年,一家老小不能团圆,那可亏大啦。
这一想,我们去阳城的决心彻底土崩瓦解。在阳城和回家之间,我们选择了后者。
我说:“刘先儿,阳城的大闺女我也不想看了。”
刘大江说:“我也不去睡那大炕啦。拐回去,撤退!”
[①] 书扣儿:也称“书扣子”,说书行话,指说书至情节紧张时暂行停住,设置的悬念。
[②] 打佛儿:河洛一带请神敬神时,一人念经,众人跟着唱和“哎嗨佛(有念兔音),嗨嗨弥”,谓之“打佛儿”,也作“打符儿”“打谱儿”。
[③] 呱哒:新安方言,有“拉家常”“扯闲话儿”的意思。
[④] 哈哧:新安土话,听音记字,随便说出来,没有什么考证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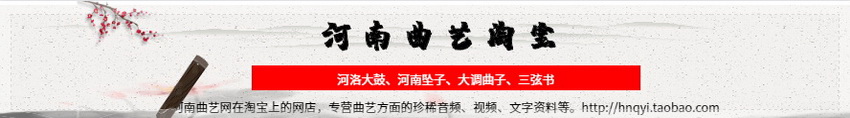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