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三十二

沙鱼沟的三天神书,我们收获满满:一是从老书筋那里学到了河洛大鼓的不少知识,受益匪浅;二是得到了比新安县书价高出数倍的报酬,发了个小财;三是神书规模大,亲戚参与者多,无形中给我们传了名,扩大了影响,为以后的生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天神书,书价36元,各种各样的“封礼儿”却达40元,竟然超过了书价本身。按理说,这应该是皆大欢喜的事儿,可是在“分账”问题上闹了个大大的不愉快。
按照出门之前事先讲好的约定,每说一家书,就分一次账。沙鱼沟书说完了,自然进入分账环节。老张为了达到目的,为了巴结、讨好尹秋花,竟然事先不同我们商量,自作主张,拿出30元硬往秋花手里塞。秋花一边躲着推辞,一边红着脸说:“叔,你这是啥意思?”
老张干笑着:“闺女,这三天书是你联系的,功劳最大,多拿点儿吧。”
秋花皱着眉头,面带不悦:“叔,出来时咱是咋说的?我一分钱不要,和你们一块出来玩的,你咋还给我这么多钱?”
我和子京心里都不满意,老张弄这叫啥事儿呢?你给儿子说媳妇心切,拿着我们大家的钱行人情,想多分给秋花一些,我们都能理解。可好歹也得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吧?不经我们同意就擅自作主,给秋花拿了大头,也太不把伙计们当回事了吧?就算76元四人均分,每人也分不到20元,你私自塞给人家30元,显然不合适嘛。就是偏向她也不是这种向法啊。
不过既然老张说出来啦,就是心里再不情愿,也要顾及一下面子,只得顺水推舟地落个人情吧。于是就劝说:“秋花,给你就接住吧。全凭你跑前跑后地联系呢,关键时候又替俺们救了场,多拿一些是应该的。”
子京也跟着附和:“就是,就数秋花出力大,多分点俺们没意见。”
尹秋花有些激动地提高了声音:“谁出的力不大?要说出力最大,还数吕老师,大书、神书几乎全是人家一个人顶下来的,你们却让我拿大头,叫我情以何堪?我说过,我是出来玩的,这钱说啥也不要。”
老张跑了一辈子江湖,却是个“死眼子[①]”,一点也看不出眉高眼低。丝毫没有察觉到尹秋花情绪的不对,仍然不识时务地生拉硬劝:“闺女,这钱说啥也得拿着,不然就对付不起大家的心意,你叔可要生气了。”
老张的“生气”不过是嘴上说说,尹秋花却真的发怒了。别看她平时有说有笑的,可一旦发起脾气,抖起威来,泼辣得有些吓人。只见她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劈手从老张手里夺过三张“大团结”,“啪”地一声,重重地摔在了老张面前,如果再靠上一点,估计能摔到他的脸上。与此同时,爆竹般地,一连串地难听话立即嘣了出来:“老张,你的啥心意?你说这啥意思?”
她一恼,一急,把称呼的“叔”立马改成老张啦:“费尽心机地把我领出来,又是买零食的,又是塞钱,不要以为你心里咋想的,打的啥算盘,别人不知道。你那点儿小九九,小聪明儿,小把戏儿,俺一清二楚!老张,今天俺把话挑明了吧。咱们在一块搭班并不是冲着你和你儿子建营的,俺们不合适,永远不可能在一起,早就没戏啦!你爷俩不用再自作多情,枉费心机,耍你们的花招儿,玩你们的阴谋诡计啦,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咱们能厮跟就多厮跟几天,不能厮跟趁早散伙!”
好家伙,这一顿连珠炮似的狂轰乱炸,只呛得老张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黑一阵,黄一阵,要多狼狈有多狼狈,要多尴尬有多尴尬。眼见得老张脸色挂不住了,被逼得理屈词穷,念及同是出门儿搁伙计,不能坐视不管啊。这个尹秋花,好起来像绵羊般地温顺,恶起来如狮子一般地凶猛。纵然老张做得不对,也不能步步紧逼,不留一点情面,让人下不来台呀。欺负老张就是欺负我们,不行,得杀杀她的气焰,灭灭她的威风,不然还不让她登上天啦?想到这里,我收起了笑容,沉下脸来,故做冷峻地质问:“秋花,你把钱摔了,是摔打谁哩?是摔给谁看哩?我们招惹你啦?我们应该看你的脸色,听你的话头儿?”
秋花一怔,脸色好看了一些,脾气有所收敛,口气也缓和了不少:“吕老师想多啦,与你俩无关,咋会摔打你们哩?”
我口气也缓了下来,但仍不依不饶:“谁也不能摔打!老张做得有不当的地方,可这么大年纪了,你不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吗?”
秋花一时语塞,脸色由阴转晴,重新恢复了笑容,立即道歉:“哎呀,俺这麦秸火脾气一上来,就不当家儿,控制不住自己啦。对不起,俺做得不对。”说着又弯腰把扔到地上的钱捡了起来,塞给老张不接,就递到了我的手里。
经过一番短兵相接地周旋、调停,“分账”风波终于平息下来。表面上似乎恢复了风平浪静,和好如初,但把老张希望的肥皂泡给刺破了,心里添了一道儿挥之不去的阴影,为之后说书班子的齐心协力,稳定和谐埋下了分裂的隐患。
沙鱼沟说书,引起小小的轰动,亲戚朋友之间的走动加快了信息传播,一传十,十传百,一股名声,四方皆知。无形的“活广告”作用非同小可,使我们自然而然,不费吹灰之力地在附近的洛口村里沟又写住了三天神书。就在刚刚站稳脚跟,说书生意逐渐向好,准备大干一番时,老张却打起了退堂鼓,无心恋战,起了“散伙”的心思。
自“分账”风波之后,虽然秋花表面上对老张仍然客气,但明显地生分和疏远起来,有意无意地拉开了距离,这使老张变得闷闷不乐。“红脸”后的种种迹象表明,秋花和他儿子建营破镜重圆的希望十分渺茫,机会几乎为零,自己以前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徒劳。再这样纠缠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到最后弄得鸡飞蛋打,身心交瘁,里外不是人。每想到此,老张就心灰意冷,釜底抽薪,彻底没有了精气神。既然儿子婚姻无望,再这样坚持毫无益处。支撑老张的念想坍塌了,自然也就没有再干下去的精神和劲头儿。
除了这个主要原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得不说,那就是老张认为我和子京都在打尹秋花的主意。老张当着我和杜子京的面公开说过:我们三人是“各怀一条心”,都想把尹秋花弄到手。俗话说:“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如今是“三人三条心,黄金也能化飞尘”啊。离心离德,这伙计还如何搁得下去?
当然,老张说的“各怀一条心”并非捕风捉影,空穴来风,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先从我身上说起吧。
沙鱼沟说书,尹秋花一段神书《韩湘子拜寿》成功地救了场,解了围,不得不让我心存感激和敬佩,不得不让我对她顿生好感,不得不让我意识到《韩湘子拜寿》的重要性,不得不让我下决心要学会这段神书,以备不时之需。对庄稼人来说,肚中有粮,心中不慌;对说书人而言,胸中藏书,脚下有路。里沟扎住书,安顿好之后,我便做出一付虔诚的样子求告尹秋花:“把你的《韩湘子拜寿》给咱抄抄,叫咱学学呗。”
尹秋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行,这段书可以抄给你,但有个交换条件,你得教会我拉弦子。”
这条件够苛刻了,谁都明白:“木头说话,三冬三夏。”“一年管子二年笙,三年弦子不好听。”拉弦子的功夫哪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学会的?哪像吹个糖稀梨儿那样简单?但我还是把胸脯拍得山响地承诺:“放心,这值啥?保证教你学会!”反正说句话累不着人,站着说话腰也不疼,教会不教会是另一码事儿,先哄着把这段书抄到手再说。
于是,白天没事儿,带上本儿,拿着笔,到尹秋花住的屋里抄书。她说一句,我写一句,遇到不明白,打住车的地方,比如这个字如何写,那句话的意思怎样讲,就要停下来请教、商量一番。过书[②]、抄书是枯燥乏味的活儿,累了,烦了,少不得穿插点儿说说笑笑的话题来调节一下气氛。这一点儿老张很是看不惯,本身因自己孩子和尹秋花的婚姻无望而感到生气,看到我们嘻嘻哈哈的样子,更是心生嫉妒,害红眼病。他认为我这个人看着老实,老实人却办些不老实事儿,不稳当,不正气,拿着抄书当晃子,打情骂俏,借机勾引人家姑娘。面对老张的误解,我不置可否,也不想做过多的狡辩。
我教秋花拉弦儿,不过是一句戏言,面子话,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付诸行动。杜子京却表现得异常积极,自报奋勇地要当秋花的拉弦老师,私下里跟她说,武成他自己都拉不好,还能教徒弟?秋花学给我听,我付之一笑:“那就让子京教吧。”暗中窃喜,反正《韩湘子拜寿》已经抄到手了,教不教拉弦儿已经无所谓了,嘻嘻。
子京就以教拉弦为借口,瞅空就往秋花的屋里摸。说是教拉弦,成晌也听不见弦子响。问之,原来还没来得及教弦子,在给秋花算卦。都是算点啥?无可奉告。子京算卦,从来不会立四柱,批八字,完全靠瞎蒙胡侃。他算卦从来都是背着我进行的,我在场时,说啥也不算。怕我扣他的“豁儿”,挑他的毛病,坏他的事儿。当然,他准备算卦时,我有意回避,做到不参与,不打听,更不会去拆他的台。至于他是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去给秋花算卦,都是说了些什么,我懒得去问,就是问了他也不会说。
子京的人格、脾气我早已领教:到哪里都是见妇女走不动路,爱喊女人的名字,亲热得能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爱央妇女帮他洗件衣服吧,补个补丁吧,做点好吃的吧,反正总要找点事儿借机套近乎。这不,自和秋花在一块的日子里,总是把“秋花”二字挂在嘴上。秋花长,秋花短,秋花鼻子秋花眼……哪一句不带“秋花”就说不成话。又是让秋花帮他拿弦子,又是让秋花帮他洗袜子,反正都是他的事儿。
知子莫若父,知徒莫若师。作为老张的徒弟,杜子京的人品,所作所为,老张焉能不知?恐怕杜子京撅起尾巴要屙啥屎,老张都一清二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杜子京用意,老张焉能不晓?杜子京以拉弦、算卦、洗袜子为由,三番五次地往秋花屋里跑,老张看在眼里,气在心里,骂在嘴上:“他妈那个逼,真不是个东西,你兄弟建营的对象也敢争!没看看你那啥材料子,不尿泡尿照照自己。”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老张追悔莫及。后悔不该攀扯我和杜子京来巩县说书。只想着让我俩搭把手,搭句腔,垫句好言,齐心协力促成他儿子的这桩婚事。谁知道适得其反,引狼入室,引火烧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但不办好事儿,反而都往各自怀里搂好处。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老张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后悔,越想越不是滋味儿。本来打算让我和子京给他们父子“做饭[③]”的,反而变成他给我们做了一锅饭,把尹秋花推送到了我们这些“虎口”里了。如果出点儿啥事儿,闯点儿啥祸,老张也脱不了干系,岂不是打不住狐子,反惹得一身骚?老张倒抽一口冷气,想想都后怕,再干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不如及早悬崖勒马吧。于是,在洛口村里沟三天神书结束之后,老张正式提出了“散伙”。
当然,以上说的原因老张绝口不提,只说是人多,班口太大,场次不好靠,书价提不上去之类的,还说自己急着回家有点关紧事儿,等等。这都是客观原因,真正的主观原因老张虽然没说,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也没有去刻意点透。
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团体,生意刚有些起色,便面临“树倒猢狲散”的残局。尹秋花只是淡淡地笑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杜子京迟疑了一下,嘟嘟囔囔地说:“老张不知发的哪门子神经……”
看得出来,子京有点依依不舍地不想解散。说实话,我也不想回啊,好不容易来巩县一趟,好不容易站住了脚儿,巩县的风景、风情还没领略够,说书界那么多仰慕的名家大腕儿还没来得及拜会,就这样拨马而回,心有不甘呐。当然,这都是富丽堂皇的理由,内心深处私底下的原因是无法说出口,也无法写到书上的,嘻嘻。
可是我们纵有千般不舍,万般不情愿,却也无可奈何。趁的是老张的手续证明,人家不干了,我们没有证明,就是想干也干不成啊。巩县没有证明,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有人寻你的事儿。
于是,我们合作一场,好聚好散,和和气气地分好账,客客气气地和尹秋花分手、道别。虽称不上《朝阳沟》里的银环 “走一步退两步,走一步一回头,山也留来水也留” ,却也免不了有几分失落和惆怅。
走了几步,尹秋花喊住了我,说有话要说。我心里“咯噔”一下,停住了脚步,老张和子京也站住了。秋花看了看他们二人,欲言又止。老张只好领着子京无趣地先走了,秋花这才问我:“你真的打算死心塌地跟他们回去?”
“不想回去又能怎样?咱没有证明啊。”我一脸的苦相,无奈地叹气。
“你要还想在巩县干,咱们搭班吧,我有办法。”
我又惊又喜,何尝不想呢?继而又问:“不会是咱俩人搭班吧?你又没证明。”
“咱俩?光咱俩就是有证明也不合适,外人会说三道四的,再说我也不会拉,开不开戏啊。”说这话时,秋花的脸稍微红了一下。
“那你有啥办法,说说听听呗。”我有点迫不及待了。
秋花说出了她的主意和打算:咱去找着廉玉民——俺老师傅廉保乾的儿子。他有证明,手续齐全,会拉会唱。咱仨人在一块儿,不是硬扎扎的班口?
“这能行吗?廉玉民俺们又不认识,两个陌生人凑在一起,互相不摸底儿,能搁成伙计吗?”我有些担心。
秋花笑笑:“尽管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在廉玉民跟前,我说话还是管用的,他不敢不听。你只用听我安排就可以啦。”
本来就不想走,话说到这份上了,还有啥可犹豫的?那就试试呗,如果不行的话,大不了多耽误几天。能多停留一天是一天吧,巩县这个地方,我有些依依难舍了。不知是留恋人,还是留恋土地,兼而有之吧。
廉玉民家住站街东边的水峪沟,和尹秋花的舅家是一个村的近邻居,中间没隔几家,几步远的距离。跟老艺人廉保乾学艺就是尹秋花舅家的牵连,据说她学说书还是舅舅给介绍的呢。
我们匆匆赶到水峪沟廉玉民家,却遭遇“铁将军”把门。秋花就跑到舅家打听,恰巧她妈今天也回娘家了,母女俩竟然意外地见了面。惊喜之余,问及廉玉民家怎么没人,告知去站街赶会去了。秋花向她妈简要地说明了情况,顺便捎带着把我介绍了一下。
老太太居然手拿着烟卷在喷云吐雾!据秋花后来说,她母亲是豫东的,所以有抽烟的习惯。得知女儿要和我在一起搭班,老太太特意迷着眼打量了一番,笑迷迷地点了点头,一副满意的样子。大概老太太一眼看出来我的一副老实相,不是鬼头蛤蟆眼的,一看就是个实在人,没有出离拐弯的心眼儿,不像啥坏人,所以感觉女儿和我这号人在一块儿还是比较放心的。临行时,老太太还再三叮咛:“书说好说赖,钱挣多挣少,都是小事儿。既然厮跟,就得搁适[④]好好的,一心一意把书说好,把生意做好,不要三心二意,吵嘴生气,让大人替你们操心。”
秋花嚷道:“你絮个啥,烦不烦?我又不是三生儿小孩儿,啥不知道,用你交待?不跟你说啦,俺们急着去找廉玉民哩。”
秋花丢下这几句话,扭头就走。我们走了几步,还听见老太太在后面嚷:“这闺女,出门可不比在家,话轻话重,横量顺长[⑤]的,娘都不给你计较。出门三里地,就是外乡人,办事说话都得掂量着,可不敢耍小性子……”再往后的话已经听不到了。唉,可怜天下父母心!
今天站街逢集会,较往日热闹了很多,大街中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两边儿地摊摆得满当当的,连个下脚的地方都不好找。买卖吆喝声、砍价声连成一片,此起彼伏。在人群多如牛毛的集市上,想找到一个人,无疑于大海捞针。
我们在大街上挤了一会儿无果,秋花让我在供销社的商店里等着,她自己出去寻找。
时候不大,便见一人气势汹汹地冲进店来,尹秋花在后面跟着。如果没猜错的话,此人肯定是廉玉民了。廉玉民一眼看见了掂着弦子的我,紧走几步,逼上前来,怒目而视:“你就是吕武成?”
我慌忙站起,迎上前去,热情地伸出手:“我就是,幸会……”
廉玉民很不友好地拒绝握手,气冲冲地推开,粗暴地打断我的话,手指几乎触到了我的鼻子:“垛子,献出来!”
“垛子”是行内黑话,指的就是演出证明。他盛气凌人地指使我,把证明拿出来查看。
“证明?没有啊。”我依然平静地回答。
廉玉民几乎在吼叫:“证明拿不出来,我把你弦子砸了!”
面对廉玉民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示威,使我的忍耐度达到了极限。我脾气好,好说话,并不代表任人可欺;我退让,一忍再忍,并不代表胆小怕事。兔子急了还敢咬人,狗急了还能跳墙,人惹急了还怕个鸟?再说你个廉玉民,精瘦精瘦,净骨头没肉的,像一根干柴,风一吹就能刮倒,细胳膊细腿儿,小鼻子小眼儿,小耳朵小嘴的,凭这点本钱还想来逞强?想打架恐怕也不是我的对手,怕你何来?不就是仗着你是当地人,坐地苗吗?有啥了不起!这个念头掠过,便有了底气、脾气,火“噌”地一下窜了上来,立即反守为攻,跳起来打开指着我鼻子的手,另一手指立即点上了他的额头,用比他还强硬几分的语气来回奉:“砸我的弦子?摸摸试试!敢动一指头,信不信我把你手给垛了!”
这几句狠话一撂,立竿见影,把廉玉民给镇住了,瞠目结舌,愣在了原地。看起来这家伙是“猛三扑”厉害,欺软怕硬。我一强硬起来,他便没了脾气。
吵的声音越来越高,招来一群围观者看热闹。我们两个像公鸡叨架般的对峙,尹秋花一直插不上手,搭不上腔。乘廉玉民一愣神的当儿,抢了过来,劈头盖脸地一顿数落:“老廉,你想干啥哩?发哪门子疯?不问青红皂白,凭啥要砸人家弦子哩?我看你是神经病又犯了吧!”
廉玉民把目标转向了秋花,冲着她嚷道:“你知道个屁!他们一班仨人,那两个都回洛阳了,他为啥还赖着不走?分明是另有所图。事儿都明摆着哩,都不知道动动脑子,好好想想,到时候把你卖吃了,还替人家数钱哩!”
尹秋花立即怼了回去:“不是他赖着不走,是我挽留的人家,你想咋着吧!”
尹秋花一句话噎得廉玉民无言以对。我借机佯作埋怨秋花:“看你介绍这都是些啥人?廉玉民久闻其名,未谋其面,听你说得天花乱坠,想着见一面,认识一下,握个手,交个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嘛,谁知道首次见面就闹得这样不愉快!算啦,谢谢你的好意,这样的朋友不交也罢,话不投机半句多,还怎么搭班合作?”又转向廉玉民,“老廉,不像你说的那样,我在这赖着不想走的,放心,不用撵,这就离开!”
我客气地拱拱手,朝着廉玉民、尹秋花以及围观者施了一个“转圈儿礼”:“谢谢诸位,惹人见笑,打拢到大家了,非常抱歉,告辞了!”说罢,不顾秋花苦苦地拉扯阻拦,毅然决然地背起行囊,拿起弦子,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商店。
“老吕别走!”廉玉民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我只作没听见,自顾往前走,并不予理会。觉得有人从后面抓住了提包,我有些愤怒地回转身,瞪着廉玉民:“你想干啥?”
“你不能走,既然打算交朋友,那这个朋友咱就交定了!常言说,‘不打不相识’嘛。既来之,则安之。既然见了面,哪能为一句话,说走就走?”说这话时,廉玉民一改刚见面时的盛气凌人,语气已经明显放缓了。
尹秋花对着廉玉民吼:“老廉,你算啥人哩!想让人家走,人家就得走;想让人家留,人家就得留?你当人家都像你一样,少脸没皮!”
廉玉民完全软了下来,换了一副笑脸:“刚才不是火头上嘛,一时说了急话、气话,算我错了不中?”
尹秋花仍然不依不饶:“火头上就该像个疯狗似的,逮住谁咬谁?急了你咋不把那屎吃两堆哩!有火气撒到别人身上算啥本事?”
真服气廉玉民能软能硬,能大能小的本事,硬起来啥难听话都说得出口,软下去恨不得给人下跪当孙子。面对尹秋花连骂带数落,一点也不恼火,一个劲儿地赔着笑脸:“老吕,你也不用生气。不是我刚才无缘无故地冲你发脾气,井里边放炮,有原因(原音)哪,说出来你可别往心里去。”
诚心诚意地拜访,却是拿热脸贴个冷屁股,还被当众抢白一顿,让人难堪,差点下不来台,能不生气,能不往心里去吗?一边忿忿地想,一边又试探着问:“你且说说,你我之间,陌路相逢,一无仇无恨,二没有宿怨,今天是怎么得罪、冲撞了,惹得你跟我过不去?”
廉玉民拉住我:“此处不是说话之地,走,走,走,借一僻静的地方。”说罢不由分说,拽住我就走,出了大街,来至无人之处,才道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他这一说,该轮到我火冒三丈,气冲斗牛了。
原来,自洛口村里沟分手之后,本来我和老张杜子京他们一前一后,相距不远,后来我和尹秋花拐路水峪沟找廉玉民耽误了时间,导致老张他们先行一步到了站街。在去往火车站的途中,恰巧被前来站街赶会的廉玉民碰上了。廉玉民见这两个人掂着弦子背着鼓,就知道遇着说书的同行了,出于职业习惯,连忙赶上前去盘诘,询问是否有证明。一打照面,发现和老张相互认识,免不了多说了几句话。
老张本来对于我不肯跟他们一道回去,而和尹秋花搅合在一起,忿忿不平,怀恨在心,却也无可奈何。毕竟脚在我腿上长着,是走是留他们作不得主。见廉玉民查验证明,猛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想出摆治我的办法了。哼,既然搁伙计的,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同厮跟着出门,一同厮跟着回家。哪像这样不顾伴儿,一个人吃独食儿!既是你无情,休怪我无义。俺们混不下去,你在巩县也休想好过,等着挨打,让人撵你滚蛋吧!老张想到这里,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奸笑:“老廉,俺俩不干了,准备回家哩,查证明没用。倒是还有一个人,留在巩县,他什么手续都没有,你一查一个准。”
“他在哪?”廉玉民问。
老张继续进谗言:“他和你的女徒弟尹秋花在一起呢,现在估计快到站街啦。”
如果说老张这一招够狠的话,杜子京还有更绝、更恶毒,更加致命的招数在等着。他失去了勾引尹秋花的机会,眼见得我和秋花在一起,更是妒火中烧,心里边一百个的不情愿,不服气,嫉妒得咬牙切齿,两个瞎眼充血。心想,我摘不到的桃子,别人也休想去摘!于是就接着老张的话茬儿,乘机诬陷:“武成他是结过婚的人了,家中有媳妇,还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来巩县勾引人家的大姑娘,这是人办的事吗?这是犯法呀!老张,咱赶紧走吧,可别闹出点啥事儿连累到咱,想走也起不离身啦。”
两个人一唱一和,说得有板有眼儿,立即激起了廉玉民的麦秸火脾气,“腾”地一下燃烧起来,二话不说,扭头就走,急得像无头苍蝇般地在大街乱撞,恨不得立刻找到目标,把我吞下肚去。正急得团团乱转时,正好碰见尹秋花找他。就立即跟了过来,发生了刚才商店里的一幕。
廉玉民还没说完,一向脾气温和的我情绪几乎失控,“呼”地一下跳了起来。我失望,我震惊,我愤怒,我想骂人,我想打架!我恨不得立即找到他们,搧他们的脸,撕他们的嘴!搧一下,问一声,栽赃陷害,良心何在?早风闻张抓子杜子京一丘之貉,一路货色,人品都不咋的,却万万没想到能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恶毒手段。
我气得嘴唇直哆嗦,说不出话来,不行,得找他们去!廉玉民怎样对付我,我就得怎样去对付他们!
[①] 死眼子:河洛方言,不灵活,呆板,不会看眼色行事的人称为“死眼子”。
[②] 过书:说书行话,把曲(书)目的内容和情节传授给对方,称之为“过书”。
[③] 做饭:这里的做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做饭,河洛方言里,特指替他人办事或提供方便。
[④] 搁适:河洛方言,同“搁合”。有“合作”“配合”之意。
[⑤] 横量顺长:河洛方言,听音记字。同“横冲直闯”“横行直走”,这里指比较随意、随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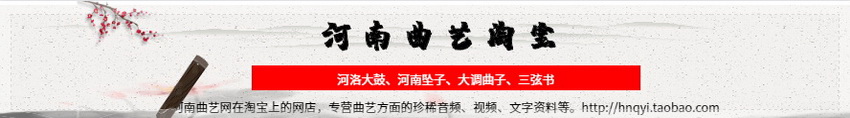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