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卅一

四人的队伍壮大了不少,也热闹了许多。多了一个尹秋花,平添不少生气,活跃了欢快的气氛。尹秋花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子,如果说在圪寮峪家中,乡里乡亲面前尚显得拘谨的话,那么离了家门,就好比俊鸟出笼,更加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了。虽然刚认识没几天,但一见如故,根本没拿我们当外人的意思,非常随意、大方,爱说爱笑,时不时地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谈笑风生,轻松愉悦,时不时一阵欢声笑语随风荡去。
怪不得谁总结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分明就是真理啊。男女在一块儿,不仅说书能提住劲儿,就连走路腰也不酸,腿也不疼,气也不喘,汗也不出了。一口气上山下岭跑个十几里,也不觉得累。就连平时走路笨得跟猪似的杜子京也能行走如飞了,你说神不神?
我们只顾高兴、开心,老张却在心里做着其他的事儿。这老家伙平时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抠得要命,一分钱掉地下,四面下钢锨,现在像脱胎换骨似的,出奇地大方、慷慨,舍得花钱。一见商店,立即钻进去,一会儿就掂上一兜子花生、瓜籽儿、糖果出来,二话不说,硬往秋花的手里塞,兜里装。秋花坚辞不受,一边推挡,一边埋怨:“叔,你这是做啥哩?俺又不是三生儿小孩儿,让你用糖果哄哩。挣钱多不容易,花这冤枉钱干啥。”
老张坚持要给:“闺女,都是小吃食儿,不值钱。年轻人嘛,爱嚼个花生粒儿,磕个瓜籽儿,解个心焦啥的。快拿着,再不接就是看不起你叔啊。”
秋花见推辞不过,只好接过袋子,说:“叔,就这一次,下不为例啊。”
秋花收了零食,既不独吞,也不专享,而是一人一大把地往下分。分给老张时,老张说,牙不好使,这玩艺儿咬不动,吃不成。只好按三个人,三一三剩一地均分了。
这可倒好,老张想花点小钱儿,用小恩小惠拉拢,用“糖衣炮弹”来腐蚀瓦解,结果,他花了钱,我们跟着秋花沾了光,享受到花生、瓜籽儿、糖果的美味,嘻嘻,悠哉乐哉!一边悠闲自得地剥着花生,津津有味地嚼着梨糕糖,一边偷偷地瞅一眼老张黑中透黄,黄中带着尴尬的面色,不仅暗自好笑。唉,老张啊,鸡不知能偷成不能,这把米反正是先要蚀出去了哈。
尽管都把尹秋花看得很高,但还是小看、低估她的能力和本事了。实践证明,不但没有拖后腿,给我们添麻烦,增加负担,相反的是,她替我们操了不少心,帮了不少忙,跑了不少腿,弄得我们反倒成了她的累赘和包袱。好像不是我们把她领出来的,领导她的,而是我们都得跟在她的后面跑,听她的指挥和调度,叫我们往东走,就不朝西去,俨然都成她的兵啦。
通过一天的接触,发现尹秋花虽然书说得一般般,却有着惊人的外交能力。她不像一般的姑娘家羞涩、腼腆,扭扭捏捏地怕见人,怕说话,怕抛头露面。逢人说话快言快语,而又把握分寸,恰到好处;待人接物大方随意,而又不失端庄,适可而止。她热情活泼,不论生人熟人,一搭腔说话,就显得亲近几分,能获得很好人缘。
毕竟她是当地人,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沟一岭,一村一店都熟悉得太多,这种优势我们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毕竟她跟着廉氏父子说书跑了两年,积累下较为广泛的人脉、人气,有不少的熟人、熟地方,哪个村子好说书,哪个地方爱还愿,她比我们要清楚得多。以上两点加上她会说话,会办事儿,会联系等,没有理由不服气,不听她的。于是,自然而然的,她成了“二导”:既是“向导”,又是“领导”,我们只有跟着她跑的份儿。
感觉我们沾光不小:不但可以分到老张“贿赂”她的零食,而且她花钱也不吝啬,每逢商店必进,分给我们一人一块冰糕消暑降温,美滋滋地品尝,凉在身上,甜在心里。更重要的是,由于她的熟人多,不是亲戚,就是朋友的,每到一个地方,吃住都能给安排得挺挺当当,根本不用我们操心,真正做到了“哪饥哪吃饭,哪黑哪住店”。更更关键的是,人家充分利用自己的关系和人脉,不动一枪一刀儿,轻易地在沙鱼沟联系到第一个还愿书——三天书价三十六,每天十二元!更更更关键的关键,这三天神书,让我们巩县之行,长了见识,开了眼界。
跟王老师在新安县说过不少还愿书,在黄河北的下冶、王屋、邵原说过不少神书。济源西山一带的神书比较简单、省事,新安、孟津一带的神书较为热闹、隆重、繁琐。如果说新安县还愿书的气派,场面足够大的话,比起巩县的还愿书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和沙鱼沟的还愿书相比,圪寮峪的三天神书系小打小闹,更不值得一提。
沙鱼沟的三天神书和新安县大同小异的地方是:第一天请神书,是开门红,是前奏;第二天敬神书,是正事儿,是重头戏,热闹高潮部分;第三天送神书,有请有送,有头有尾,圆满结局。巩县的神书更细致,更讲究,更隆重,更繁琐,对说书的要求更苛刻。对说书人也是一种考验:如果肚子里不装几十段儿各式各样的神书,就应付不了各式各样的场景;如果没有两把棕刷儿,就不要冒充什么神仙 ;如果没有锋利的“金钢钻”,千万别揽难钻的“瓷器活儿”。当然,说书的虽然操心大,出力多,受麻烦,受啰嗦,但毕竟是招待好,书价高,封“礼儿”多,钱不少,最后还是花算的嘛。
巩县说神书,无疑于红白大事。这不,主家一边安排买肉和香箔纸钱,忙着搁油锅,炸果子[①],蒸贡香[②],准备贡菜[③]等,一边派人给亲戚“报信儿”。巩县一带的神书习俗,一旦还愿,四邻八舍,三亲六故的都得通知到,不能遗漏和失礼。那时候打不成电话,发不了微信,交通工具也不发达,亲戚远了怎么通知呢?很简单,家人不够用了,委派家族关系最近的“紧门儿”,甚至央求街坊邻居帮忙,掂起两条腿,启动11号车,翻山越岭地跑去传话、送信儿。七大姑姑八大姨,八大姨家干闺女,干闺女家续女婿……哪一家儿都不能少。所有远亲近邻的,但凡收到“口信儿”,无论事儿再多再忙,都暂且搁置,携带礼品、贡品赶来参加还愿盛会。巩县把人情世故,礼尚往来看得很重。
第一天神书和新安县的区别不大,无非是请神轴子,写神牌位,一应供品摆齐,请神、安神,我们说请神书,晚上除上垫场说一段神书外,还照样开大书,一宿无话。
热闹的就在第二天的“正事儿”。说书的虽称不上“昼伏夜出”,却也是晚上熬半夜,早起睡懒觉的“夜猫子”,没事儿时一般不睡到八九点,日头晒不住屁股是不会起床的。当然,今天还不等太阳照到床前,就被外面闹喧喧的声音从睡梦中硬是给吵醒了。一时好奇,睡意全无,一骨碌爬起,来到院里一看,乖乖,好一派热闹景象!
这哪里是在还愿,分明像在娶媳妇!不知什么时候,院里靠厨房门口已经支起了两三盤红白大事儿才能用到的大号风灶火[④],有蒸馍,有炒菜,有烧水的。请来帮忙做饭的几个大师傅掂勺子,拿菜刀,烧的烧,燎的燎,煎的煎,炒的炒,榷的榷,捣的捣,端的端,跑的跑,忙得不亦乐乎。院当中拉开了七八张八仙桌,四周摆放着板凳,是做餐桌待客用的。靠正窑门口放着的两张八仙桌,一张摆满贡品,一张安放着香炉、蜡烛、香箔等,显然是请神、敬神专用的“神案”,有几个应邀而来的神婆已经在烧香、磕头、念经了。
打发我们吃罢早饭,本村帮忙的自不必说,远处的亲戚也开始陆陆续续地赶到。宽敞的农家小院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不亚于香烟庙会的规模和场景。每响起一阵鞭炮声,便是哪一家亲戚来了,主家慌忙出去迎接进来。每来一家亲戚进院,二话不说,都先到神案前安放好自己所带的贡品,虔诚地燃上三支香,恭恭敬敬地跪下磕仨头,然后才做其他事儿。
第一次见如此盛大、庄严、隆重的还愿场面,激动、振奋之余,一向不怯场,“人来疯”的我也不禁手心里捏了一把汗,心提到了嗓子眼里。这么大的场合,这么多的听众,能应付得了吗?如果把书说砸了,出丑了,那可是秆草捆老头,丢个大人啦。事到临头,怕也无用,只有调整心态,摩拳擦掌,充分准备,沉着应战吧。
巩县还愿书对时间要求真是严格,第二天的敬神书必须在正午的十二点准时开书,多一分嫌迟,早一分不行。神婆们提前把香烧上,贡品摆齐,一切准备停当,我们提前把鼓支好,弦子定准,各就其位,各执其事。主家提前备上一个大“封儿”,连同用红布包好的四盒带把儿好烟一块儿放在说书桌上。主事人时不时地抬腕看看手表,又看看桌子上放的座钟,时间对好,唯恐出现差错。单等十二点正当午时已到,主事人一挥手:“开书!”一声令下,鞭炮声噼哩噼啦响起,与此同时,三声鼓响,弦乐齐鸣。杜子京的“十八板”使出了浑身解数,身体抖动之剧烈,脑袋摇晃幅度之大,抽弓送弓的力度之猛,让尹秋花抿着嘴偷笑,让听众瞠目结舌。可能他们从没有见过如此投入、卖力的拉家吧。一曲下来,掌声、鞭炮声交织在一起。
敬神书唱的是《龙三姐拜寿》。关于这段书我是有把握说成功的,因为小出身时王老师抄的第一段书就是《龙三姐拜寿》,也是最早学的,被老师指点来,掰捏去的段子,后来又吸收了刘大江的演唱之长,来补自己的不足之短,更加完善了。只所以喜欢说这一段儿,因为该书占路儿很宽,应用广泛,无论是婚庆祝寿书、满月贺喜书、发财书、平安书、祈福书、祈雨还愿书等等,皆可适应。虽是神书,说与人听,却能叫人向善,起到“行善总比作恶强”的警示作用。是老少皆宜,人神共享的一段好书。尤其是唱到最后两句“积德行善办好事儿,龙三姐跑到你家门”时,很能挠到主家的心窝里。但凡请神还愿,烧香念经之家,哪一个不喜欢听做好事,做善事的话题?所以唱到最后,无论是主家,还是神婆,彼此会意,相视一笑,又相互点点头,流露出非常满意的神情。
新安县的大型还愿书也有亲戚朋友携带香箔贡品风尘仆仆赶来参与的情形,但大多是神前上香、磕头,献上贡品即可,极少要求说书人额外给客人说神书。巩县则不然,客人除了敬神路数之外,还要请说书人以客人的名义送上一段神书。说白了,就是这段神书不是给主家说的,而是给客人说的。既是给客人说的,就得请人家说明意愿、事由等,以便对症下药,量体裁衣,掂量该说什么书,不该说什么书。当然,给客人说神书也不是白说的,是要封“礼儿”的。有的客人还要“点书”,要求说书人根据自己心愿说某某神书,如果能达到客人满意,封的“礼儿”会加倍。
正场敬神书说罢,第一家客人登场,先是在神前上香、烧纸、摆供、磕头,然后站起,不慌不忙地度到说书桌前,问道:“说书的会说《吕洞宾戏牡丹》不会?如果能说,就来这一段儿吧。”
我点点头:“说得不好,但是能说成。”
“好!”对方很是高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块,当众公开亮了亮,再用红纸封好,放在说书桌上,“开始吧!”
虽然我是头一次经历巩县这样大的说书场面,但事先已经听老张说过,尹秋花也详细地介绍过巩县说神书的风俗和礼节。对客人“点书”的习俗,虽不敢说胸有成竹,却也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尽量做出很懂,很老练的样子,待鞭炮放过,沉稳开唱。
谢天谢地,幸好几个客人点的几段神书都是我熟悉能唱的,除了《洞宾戏牡丹》,还有《观音母开花店》《八仙庆寿》《白猿盗果》《道童修仙》等,这些基本不在话下,几个红包顺利地拿了下来,就在沾沾自喜,有些飘飘然时,猛然打住了车,卡住了壳,弄得差点让人下不来台了。
唉,最后一个客人也真是的,放着那么多我会说的神书不点,偏偏要往我的软肋上戳:“哎,说书的,来一段儿《韩湘子拜寿》吧。”此言一出,我的脑门上直想冒冷汗。听说过有《韩湘子拜寿》这段神书,也叫《韩湘子讨封》,却从来没有听人唱过。俺老师不会,所有厮跟过的同行也不会。大概意思不知道,照着那一角子蒙也没法蒙啊。再说既然人家敢点,肯定是懂的,瞎侃胡抡是行不通的,难堪是小事儿,弄不好就丢大人了。
就在抓耳挠腮,不知如何应对时,有人替我答应下来:“好!”谁?尹秋花。她不露声色,极为平静地说:“吕老师说几段了,太累啦,过来歇一会儿吧,让我替你说。”我既怀疑又感激地看着她,意思是:你能行吗?
尹秋花自信地站起,冲我点了点头。我连忙离座让贤,秋花一首定场神诗道过,钢打弦拉,不慌不忙地唱了起来:
山长青松松罩山,山中有洞洞藏仙。
山中有洞人能见,洞里藏仙见着难。
昔日里有一个韩湘子,一本本修仙终南山。
终南山上得了道,就是长生不老仙。
……
嘿,她这一段儿《韩湘子拜寿》唱得还真不错,相当熟练。尽管还不是特别精彩,仍像在背书,在我听来,却如潺潺的流水那般入耳,像习习的凉风掠过心头,让人惬意。她很轻松自然地救了场,不声不响地解了危,过渡自然,让听众丝毫没有察觉到我的“黔驴技穷”,不会说这段神书的难堪。一句“吕老师太累啦”,让人心里暖暖的,让头上的冷汗被大家理解成累出来的“慌汗”,一切都是天衣无缝。凭人家在紧急关头,应接不暇时,挺身而出地替我抵挡一阵,无论如何都得心存感激。不仅对这个女子的魅力更加另眼相看,甚至都有点佩服和敬慕了。
凭经验都知道,巩县的还愿书只要第二天的重头戏熬过去,第三天临近收尾儿,远没有前一天的隆重、繁琐,说书人相对轻松了好多。晚上刹罢书,躺在床上,终于可以舒上一口气,美美地地睡上一觉,做个好梦啦。
这一觉睡得香,睡得安稳,临天明时却做了一个梦。梦见又来了一班说书的,在当院拉开书场,和我们“怼书”。领书的是一红衣女子,长发飘飘,红裙飘飘,折扇上的红缨飘飘,飘飘如仙。唱腔飘飘,琴声飘飘,动听的歌喉,优美的旋律,宛如天籁之音,随风飘来飘去,钻进耳朵里,往外拔都拔不出来。只听得让人陶醉,让人迷失自我,让人失去了底气,让人无心恋战。心里一急,梦中惊醒,耳边说书声并没有随梦散去、消失,反而愈加清晰、逼真。奇了,怪了,难道活见鬼了,产生错觉了?侧耳细听,确确实实地有女子说书声自院中传来。是秋花晨起练功?显然不是。秋花嗓音不及此女声浑厚、有磁性,耐寻味儿。难道真的是天降说书的?神话故事要在现实中发生?一刹间睡意全无,好奇心驱使我立即爬将起来,急匆匆跑出屋门一看,不禁哑然失笑:院子里的小吃饭桌上放着一个收录机,女子说书的声音便是从那个长方盒子里飘了出来。
八十年代,盒式录音机还没有普及,尤其在农村,更是稀罕物,不是一般人都能拥有的。而让我们感到惊喜和稀奇的是,录音机里放出来的是真实的,正宗的,不折不扣的河洛大鼓!
河洛大鼓是土生土长的民间说书,很少登得大雅之堂,能上广播电台的更是寥若辰星。早在跟老师学徒时,收听过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播放,段界平演唱的河洛大鼓《拳打镇关西》,仅此一次,还是只听了个尾巴,没听过开头。就这俺老师他们也是激动兴奋得不得了。如果说段界平是领军人物,站在革新的前沿,其河洛大鼓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话,则眼前听到的河洛大鼓更接地气,更原汁原味,让作为同行的我们更是亲切、熟悉。因为是女子说书,对我们则更具吸引力。
这不,说书声吸引得老张揉着眼睛出来了,杜子京没人领路,也用棍捣着,摸索着出来了。来两三天了,可能大家都在为还愿书忙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听录音机吧。今天有空了,主家才把录音机放开,大概是图个热闹高兴吧。这一下却让我们得以发现“新大陆”。
把录音机搬到当院听书的,并不是年轻主家,而是主家他爹,河洛一带都习惯上称之为“老掌柜”。是一个六十多岁,高高大大,身材魁梧,浓眉大眼,鼻直口阔,精神矍铄,气宇不凡的老者,乍一看就不像农村种地的庄稼老粗,倒有退休干部的气质和派头。老者冲我们点点头,招呼坐下,很是热情温和地说:“咋着,把你们都吵醒了吧?”
杜子京连忙说:“没有,没有,是这说书说得太好听了,把俺们吸引起来啦。老先儿,这是哪里的说家儿?还是人家的书,说得有劲儿,听着有味儿。”
老者笑笑:“巩县年轻一蕟(fà)儿[⑤]中有名的女说家儿,竹林的李新芬,你们不认识?”
老张说:“李新芬?听说过,是好说家儿,可是没有见过,也没听她说过书,今天头一次听到录音,真是开眼界啦。”
杜子京听着录音,一副入迷、崇拜的神情。这家伙太贪,听听李新芬的书,过过耳瘾就可以啦,尚不满足,得寸进尺,竟然想得到这盘磁带。便试探着问:“老先儿,这盘磁带在哪能买到?”
“哪里也买不到,市场上没有卖的。这是李新芬在穆沟说书时,有人拿录音机现场实录的,就这一盘儿。”老者回答。
子京又拉着脸皮求告:“老先儿,这盘磁带我老想听啊。能不能高价卖给我,出再多的钱都中。”
老者摇了摇头:“就这一盘儿,说啥都不会卖给你。”
我明白,杜子京想要这盘磁带是不可能得手的。君子不夺他人所爱,你老杜大年初一借袍子,没想想,借给你,人家咋穿?所以,尽管我也有点“爱不释耳”,还是不敢张口求借。人家把磁带拿出来,放给我们欣赏欣赏,已经很知足了。
我说:“巩县的 ‘好说家儿’李新芬,早有久仰,却从未谋面,更没听过她说的书。谢谢老先生,让我们听到了她的磁带。”
老者笑笑:“名师出高徒,她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张明党,你们会没听说过?”
张明党这个名字不但听说过,而且如雷贯耳。不仅是听老张介绍,刚下火车站街亮书时,就有当地人说起过张明党。民间有传言:“听过张明党的戏,一辈子不生气,听明党说几句儿,一辈子不害病儿。”可见知名度之高,影响力之大,已经达到了妇孺皆知的境界了。
见我们惊奇的样子,老者一副淡然、司空见惯的神情:“巩县出名的年轻女说家儿多得是,各有特色,各具千秋,大都师出名门。像小官乡水道口的牛会玲,腔特别好,吐字又清,唱起来气势磅礴,一道弦既能唱坠子,又能唱大鼓。她是巩县数得着的说书名家崔坤的得意弟子,人家有文化,唱词又讲究,年年轻轻的,装了一肚子的书,唱到哪,响到哪。还有南河渡的‘好说家儿’张妮儿收那个徒弟黄金焕这两年也崭露头角,脱颖而出,人年轻漂亮,腔也俏丽,到哪都能叫好。”
“张妮儿也是‘女说家儿’吗?”我插话。
老者笑道:“听名字好像是女的,实际是男的。在过去男孩儿父母待得太娇,才有意取了个女孩儿的名字。他有大名,叫林森,但人们还是习惯喊他的小名。巩县说书的,提起张林森,鲜有人知,提起张妮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出名。”
老人很健谈,一旦打开了话匣子,一发而不可收;老人是个说书通,提起巩县的说书艺人,如数家珍,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交谈中,惊讶地发现,老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迷”,真真正正的“书筋”。我从艺以来听过的,没听过的,知道的,不知道的,学过的,没学过的,大本头,长短篇,小书帽儿,垫场段儿,文书,武书,苦书,耍笑书,翻针线筐儿书……老者都能说出个子午卯酉,让我们所谓以说书为业,专业吃这门衣饭的自叹弗如,自觉惭愧。老人说,他听了一辈子的书,好说家儿,瞎说家儿,大干家儿,小打小闹小戳腾,大家、名家,无名之辈……什么样的书他没听过,什么样的说书人他没见过?
我相信老人说得是真的,没有夸张和水分。因为他说的有关说书的每一件事儿都让人不容置疑和信服。我们只有洗耳恭听、点头的份儿,而没有摇头的理由。
老人接住刚才的话题:“巩县这一蕟儿‘大干家儿’‘名说家儿’除了张明党、崔坤、张妮儿外,还有很多。如:西半县回郭镇的杨氏两兄弟——杨大会、杨二会;老家涉村,后来迁住登封的说书世家王圪塔(王周道);站街集沟的好说家儿,徒弟们桃李遍天下的狄德有……
“咱巩县历来就好听说书,尤其是好听鼓书,其它的像坠子、琴书啥的到咱这都吃不开,打不出,唱不响。老一蕟儿说书的有个老刘先儿(刘林)是站街小黄冶村的。有一年从豫东过来了八个唱坠子的女说家儿,一个比一个年轻,一个比一个漂亮。人长得漂亮,坠子唱得也漂亮,在站街说书轰住摊儿,唱叫好啦,不服气坠子能比不过鼓书?想在巩县打开门事儿,闯开市场。老刘先儿听说唱坠子的来抢饭碗,很生气,就来到站街摆开书场和八个唱坠子的女艺人对棚。唱了不到半个钟头,硬是把八个唱坠子的给比下去了,灰溜溜地收拾东西离开。从此‘一人斗败八个唱坠子’的佳话在巩县传为美谈。
“咱巩县历来就好听说书,自然也是说书人名家辈出的地方。听老辈人说,咱现在听到的鼓书是洛阳偃师唱琴书的艺人从南阳带过来的,最早是单打鼓,干唱的,没有弦儿,后来加进了洛阳琴书的杨琴,叫‘鼓碰弦’。虽然鼓书的根儿是偃师的,最早的头一蕟儿‘老干家儿’段先儿(段炎)、胡先儿(胡南方)、吕先儿(吕禄)、高先儿(高廷章)、李先儿(李富路),家都是偃师的,可是轮到第二蕟‘说家儿’,却大多都出在巩县。像康店叶岭的叶刺猬,就是段先儿在巩县说书时收的高徒。小黄冶的刘林是跟着老吕先儿学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至第三蕟、第四蕟、第五蕟时,巩县的好说家儿越来越多,已经赶超偃师。像李宏民、杨翠典、陈夯(陈庭照)、张大科、张新有、翟建立……都很出名。要不人们都说,咱的大鼓书,源于偃师,兴于巩县呢。”
老者越说越有劲儿,我越听越入迷。心里面除了惊讶、赞叹,就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哪里是“说书通”?分明就是河洛大鼓的“数据库”“活字典”啊!他的肚子里装着河洛大鼓的一本“流水账”。他把河洛大鼓的前生后世,百年兴衰叙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简直就是通晓河洛大鼓史的当代司马迁啊。这些知识,从老师那里一辈子不可能学到,从书本上永远不可能读到。方信“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此言不谬也。听老者一番话,不枉来巩县说书一回,无论是否成功,能否挣到钱,都感觉不虚此行。
[①] 果子:这里所说的“果子”是用面片儿切条儿再折叠(有的不折叠)做成的油炸食品,多作祭祀、敬神的贡(供)品。
[②] 贡香:用面制作,专用于祭祀、敬神做贡品的各种形状,各种花型的蒸馍,称“贡香”或“供香”。
[③] 贡菜:用于祭祀和敬神所做的菜品称为“贡菜”或“供菜”。
[④] 风灶火:河洛方言中,把红白大事中临时盘起的专用大号烧煤火(有的地方是烧柴的)称为“风灶火”。
[⑤] 一蕟儿:河洛方言,听音记字,指同一阶段,同一时期或同一类型的人或事物。也称“一茬儿”“一沷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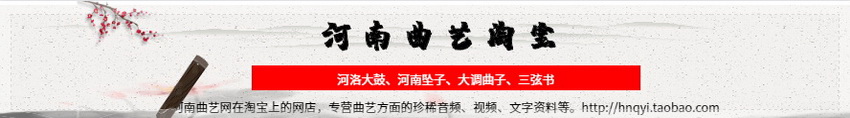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