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五十一

王金红创建河洛大鼓QQ群的初衷,不仅仅是聚拢河洛大鼓艺人、爱好者,在群里聊天互动,沟通交流。张罗群友见面会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大伙儿在一块吃个饭,拉个家常,互相认识一下。其实她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和计划想通过QQ群和群友见面会来付诸实施,那就是想为河洛大鼓造一本“家谱”。
早在建群之前,金红就和我商量过此事儿。为河洛大鼓界艺人修谱儿的想法,是受义父肖巍为相声续修“家谱”的影响。
说起洛阳的相声名家肖巍,那可是赫赫有名,震震有声。萧巍,艺名明巍,字高山,号拼命三郎。师承两大门派:一派为邱祖龙门(牌)派,系第二十代弟子,师父汪元亮;一派为相声门派,系第八代弟子,师父赵振铎。有着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华山东快书研究会理事、河南省曲艺家协会理事、洛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洛阳市书法家协会会员等名头。作品曲目三百余篇,获国内各种大奖五十余项(次),入选《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曲艺界人名大辞典》等。
家有家谱,行有行谱,不过行谱也称为“家谱”。相声界的“家谱”也就是曲艺行当常说的“谱系表”或“传承谱系图”,说得明白一点相当于行业的“家庭成员档案表”。一份完整的传承谱系记载着曲艺行业内每个行艺人员的师承关系、隶属门派、辈分高低等重要信息。
相声界修造家谱史上已有两次:一次是马三立老先生创修的,见于1985年出版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一次是1995年出版的《中国相声史》上刊登的“相声演员师承关系表”。肖巍之所以要张罗着续修谱,一是因为目前传下来的这两种行业档案,存在有谬误、矛盾和各种争议,急需更正和统一说法。二是早期的家谱因受信息闭塞的局限,多有遗漏。随着相声队伍不断发展壮大,通讯网络日益发达,原来存在的谱系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节奏。三是肖巍在相声行内有一定的声望,且对相声的发展历史,师承关系多有研究,具备续谱的条件和能力。鉴于此,加上肖巍对相声事业的热心和责任感,续修家谱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他的肩上。
金红在洛阳曲艺界很熟,从小又认到肖巍跟前做了干女儿,关系自然更近,平时多有来往。这次相声续谱,肖巍跟金红说:“你们的河洛大鼓也应该有一份‘家谱’呀。有了传承谱系,才能理清来龙去脉,发展衍变。无源不盛,无根不兴。弄清自己从哪来,才能知道应该往哪去。趁现在有些老艺人还健在,赶紧着手吧,再晚就来不及啦。河洛大鼓界我很熟,段界平、王小岳俺们都有过交集,必要的话,我也可以帮你。”
经义父一番撺掇,金红有点动心,想想很有道理。想为河洛大鼓做点什么,这也是很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儿,而且稍纵即逝,时不我待。金红有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于是先找我商量给河洛大鼓写“家谱”的事儿。
其实早在创办网站,写《河洛大鼓》一书之前,已经开始留意,并搜集整理河洛大鼓的源流、传承脉胳及各代传人等相关信息了。并在粗浅研究的基础上,在网站和博客发表过《河洛大鼓传承脉胳》和《河洛大鼓各代艺人简介》,又将这两篇纳入拙著《河洛大鼓》。此后的这些年,一直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这方面的资料掌握了不少,并小有成果。
这些年来,在茫茫的网络海洋里大海捞针般地捕捉相关信息,反复甄选,去伪存真。这些年来,尽可能地接触、走访同行艺人,不厌其烦,刨根问底,抓住稍纵即逝的记忆碎片。这些年来,捕风捉影,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捕风问从何刮起,捉影追影后之形,沿蛛丝理清脉胳,顺马迹追溯其踪。总之,这方面不知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汗,搭了多少闲功夫,做了多少有用功和无用功,连我自己也统计不出来了。
有的说啦:这些本该是那些相关领域的,有资质的专家、学者所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更应是那些领着国家俸禄,拿着固定工资的非遗保护中心的领导者、白领们该做的事儿。天塌有地顶,一个底层草根艺人,咸吃萝卜淡操心,该是你瞎出力、白忙活的事吗?
说得也是。知道本不是自己该管的事儿,可就是生来心贱、手贱,忍不住啊。不去想心痒,不去做手痒。一种对河洛大鼓难以割舍的情结驱使自己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而且着了魔,中了毒瘾似的,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这些年来,这种没有回报,不见经济效益的事儿少人问津,都是自己在孤独中负重前行,如今有人加盟,求索路上多了同行者,携手同进,这是天大的求之不得的好事呀!肖魏老师和金红的构想,岂不是我正在做或正想做的事儿?
然而,欣慰的同时,为了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彼此之间合作得更愉快,更持久,更成功。就得先丑后不丑,丑话说前头。就得先泼冷水,把困难摆在前头,是知难激进,还是识难而退,先做抉择。以免虚张声势,虎头蛇尾,半途而废,不了了之,落下笑柄。做这件事儿不是单凭一腔热情,一时心血来潮,就能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锲而不舍的耐心和勇气。从我过往的路,经历的失败,栽过的跟头,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不得不先打一剂预防针,把修续家谱的种种困难摊在金红的面前:
“金红啊,你得先想清楚,为河洛大鼓做家谱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是相当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事先得充分考虑遇到的困难和棘手的事情。首先是河洛大鼓流传地域广,辐射面积大,艺人居住分散。洛阳的偃师、新安、孟津、宜阳、汝阳、嵩县、伊川、栾川,郑州的巩义、荥阳、登封,甚至三门峡的渑池、义马,黄河北的沁阳、温县、孟州、济源等。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艺人,逐个采访,摸底排查,统计整理起来工作量可是相当巨大啊。”
“呵呵,吕老师放心,这些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河洛大鼓涉及四市(洛阳市、郑州市、三门峡市、济源市)十几个县,无以数计的艺人。如果一两个人去跑这事儿,恐怕累死也忙不过来。既然打算做这事儿,就不是你我一两个人的事儿,是大家的事儿,是河洛大鼓的事儿。咱们就得发动大伙儿,携起手来,群策群力,众志成城,众人拾些火焰高,共同打造一份咱河洛大鼓人自己的家谱。咱就以河洛大鼓QQ群为平台,召集、组织河洛大鼓艺人中有热心,有责任心,有传承意识,有能力的老师们行动起来,共同参与搜集和整理家谱资料,各自分工,相互合作,然后汇总成篇。比如——这是咱私下商量的嘛:可以让肖巍伯负责洛阳这一块儿,张怀生老师负责偃师,尚继业老师负责巩义,潘红团老师负责汝阳。小党(党俊乐)、(朱)继鹏年轻,活动能力强,就让他俩负责洛阳南面的宜阳、嵩县、栾川等地。我负责郑州,你嘛,多受点劳儿,负责你老家新安县,再捎带着焦作的温孟滩,还有沁阳和济源。”
哈哈,看来“家谱”的事儿,金红不只是随口一说,也并非是打无准备之仗,而是早已深思熟虑、胸有成竹了。看她规划得头头是道,安排得风雨不透,不得不佩服她的周密细致,但还得继续摆困难:
“你这样安排够周到了,可考虑过河洛大鼓传承谱系的复杂性没有?复杂得剪不断,理还乱,让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整理记录带来很大的难度。”
“啊,是吗?这我还真没考虑过。怎么个复杂法,说说看呗。”
“相声界的师徒传承是否循规蹈矩,乱不乱?隔行如隔山,咱是行外人,不懂不能乱说。但河洛大鼓界的传承谱系混乱得很,争议颇多。河洛大鼓艺人中,有的尊邱祖为先,有的敬三皇为祖,有的以子路为师。这些都是远古的事儿,不考究也罢。可近代的师承机制也很紊乱,谱系之间相互矛盾,彼此抵触,难自圆其说的现象比比皆是。解放前的拜师学艺还比较规范,建国后逐渐淡化,尤其‘文革’间被视为封建礼教被禁忌。后来文化部门举办的曲艺学习班,一人教,数人学,是教师和学员的关系呢,还是算传承意义上的师徒关系?莫衷一是。但凡名家,为纳百家所长,大都不只投拜一个师傅,从而形成了既承于A,又延于B的两支互相交叉的传承谱系,以何为准,不好把握。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洛大鼓国家级传承人陆四辈老师。陆家和你们王家一样,都是有名的大鼓世家。陆老师的爷爷陆明智老前辈拜河洛大鼓第一代艺人李富路为师,是不折不扣的河洛大鼓第二代传人,传至第三代陆庚照,到了陆四辈老师那里应该是第四代传人,这没毛病吧?可是陆老师慕名河洛大鼓第二代名家张天倍,就正式拜其门下成为弟子。陆老师口中常常提及,念念不忘的‘俺师父’指的不是自己的父亲陆庚照,而是张天倍。那么问题来了:按陆家大鼓世家来推,陆四辈老师应该是第四代传人。按投师第二代艺人张天倍来说,则提了一个辈分,成了第三代传人。是以门内出身为准,还是以严格的师承为是,难以定论。再如河洛大鼓一代宗师段界平,早先投第三代艺人杨二会老前辈,还跟你爷爷学艺仨月,按辈分推,应该是第四代传人吧。可他后来又磕头跪拜张天倍为师,则成了第三代传人,和老师杨二会平起平坐了。为此你爷爷还兴师问罪,骂他‘欺师灭祖’。名家尚如此,其他的就更乱了。类似情形,不胜枚举。这种交叉传承,一方面促进了各流派之间的交融、借鉴和提高,另一方面增加了传承谱系的争议性、复杂性,给后人的整理、记录和研究带来困惑,陡增难度。”
“哎呀,吕老师,你不说,我还真想不到,河洛大鼓的传承谱系搞起来还有这样多的事哩。可咱怕麻烦,现在不搞,拖得年代越久,越来越说不清楚了,就更加麻缠,解也解不了,抖也抖不开,成了个死结。所以说,咱现在解疙瘩,免得给后人添疑团。是这样吧,咱先依据现在调查结果如实记录整理。遇到有争议的疑点,可在QQ群里广泛征取业内老师们的意见,力求达成共识。必要的话,可以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定夺。你看可以吗?”
“嗯,这样做比较稳妥些。还有的就是,河洛大鼓仅有百余年的历史,流传至今最多也不过经历了六七代艺人。其传承谱系相应较为单薄,整理出来的‘家谱’无论如何详尽、完整,充其量只能是一份留存的珍贵资料,难以成书传世。”
“是呀,单纯的家谱都不太长。我见过相声的家谱,不过是信纸写了十几页,当然跟出版一本书相距甚远。吕老师还有其他想法?”
于是,我就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当年撰写《河洛大鼓》一书时,自以为对自己从事的河洛大鼓已经知道得够多,了解得够透彻,掌握的素材够丰富了。虽然该书对河洛大鼓的形成、历史、源流、传承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对其曲目、音乐及演绎方式等内容也有所触及。但局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和环境条件,以当今发展中的眼光来看,这部处女作《河洛大鼓》只能算入门级的“初探”,略显青涩,尚欠成熟。随着这些年知识不断积累,视野不断开阔,接触面更加宽泛,结交认识的同行艺人更多,接二连三不断地发现“新大陆”,不断地颠覆着传统的认知。回头来再去看这本《河洛大鼓》,尚存粗略,有挂一漏百之嫌,由于当时排版原因,甚至还有张冠李戴的失误。但数年过去,木已成舟,书已定局,已经没有补充完善,修正纠错的机会。鉴于此,一个更宏大的构想早在胸中酝酿,那就是编纂一部《河洛大鼓志》。
为一个曲种立志,以专志的体裁来记述民间曲艺河洛大鼓,无论在文学史上,还是曲艺史上,甚至是专业史志领域,都没有先例可循。不得不权衡再三,慎重考虑,自己是否具备编撰志书的能力和条件。
编志书不比写小说,允许虚构,放飞想象的翅膀,想到哪写到哪,信马由缰,任其自由驰骋。志书是严谨的,以事实为依据,一是一,二是二,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水分,更不能瞎编胡侃,信口开河。写专志更不比写专著或学术论文,可以研究、分析、推理,想当然地得出自己的论断或观点儿。志书讲究只述不论,不允许以点带面,以偏概全,不以自己的喜好而左右笔端。总之,编志书远比做小说,写论著要难得多。尽管此前曾主编或参编过《寺上村志》《孟州市移民安置志》,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懂得了志书的一些要领和规范,可单挑大梁,独手成志,来啃这块硬骨头,仍感到底气不足,力不从心。虽蓄谋已久,跃跃欲试,却踌躇不定,迟迟不敢付诸行动。
《河洛大鼓志》内容应该很宽泛,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是立志,传承谱系首当其冲,重中之重。既是单独一份“家谱”单丝不成线,独谱难成书,何不汇溪流归大海,谱志相融成一统?将家谱纳入《河洛大鼓志》,一来没有了传承谱系单薄的烦恼,二来齐心协力,众手成志,壮大了《河洛大鼓志》的编纂力量。可谓相得益彰,何乐而不为呢?
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时,金红十分震惊:“哎呀,吕老师,太了不起啦!我们所想的,你却早已赶在我们前面了,而且谋划更长远,考虑更全面,真是大手笔!能全面系统地记述河洛大鼓的发展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那是再好不过啦。吕老师,就依你的规划,抓紧行动吧。我们全力配合,坚决支持。”
金红采纳了我的建议,统一了意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编纂《河洛大鼓志》就更增加了信心和底气。
金红继续说道:“吕老师,你只管放手去做,我们鼎力相助。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帮忙解决。需要查找相关资料,郑州、洛阳的图书馆、档案室我都有熟人。书稿出来后,审校、出版的事儿也不用愁,我有这方面的朋友。到时候不用你操心,交由我来办理。”
金红的一番话,不只是给我鼓足了劲儿,加足了油,还解决了最终出版的后顾之忧,使我不再含糊,不再犹豫,把心装到肚子里,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地投入到《河洛大鼓志》的编撰之中。
编志的事儿,金红之所以暂时没在QQ群公开,是因为她觉得还没找到适宜的时机。之所以没在群友见面会上提及,是因为相关人员没能到场,加之那天时间仓促,大家忙着叙旧,倒把这事儿给忽略了。但“为河洛大鼓书写一份家谱”的事儿让洛阳日报记者杨玉梅通过一篇通讯报道《让河洛大鼓永远唱响在河洛大地》给传播开来,还惊动了洛阳市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的相关领导,并纷纷表示支持。影响如此大,感觉这件事儿已经很难搁置下来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时有瞬息万变。方案既定,还未实施,金红还没来得及通知、召集相关人员具体安排分工事宜,就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故。此次修“家谱”的最早发起人,金红的义父肖巍老师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送进了重症抢救室。这一躺在病床上再没起来,直至不幸离世。可叹一代名家:“壮志未酬身先死,续谱大业靠何人!”相声续谱尚且搁浅,河洛大鼓更无从谈起。作为两家世交,又是干女儿,金红同亲生子女一样奔波于医院之间,忙得心力交瘁,哪还顾及其他?
肖巍老师的故去,对金红的情绪影响很大。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提及编志续谱的事儿,好像根本就没发生过一样。一来她经营着一家传媒公司,还要在单位上班,事儿确实多,忙得无暇顾及;二来义父的去世,似乎让她失去了修谱的信念和精神支柱,把这一切看淡了,漠然处之。当然这第二条是我胡猜测的。总之,编志的事儿,她把底火给烧起来了,却不再加油添柴了;她把我搊[1]上马却扬长而去,让我骑上马下不来鞍了。原踌躇满志,谋划出来的浩浩荡荡编志大军不见哪里去了,一转眼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又是孤家寡人一个,你说这叫什么事呢。
有的说,有啥下不来鞍哩,学会放下,绝对不会有人不依你吧?别人都能放下,可我放不下了。如果能放下,那就不是我了。认定的路,不管别人走不走,反正就要一条道上闯到黑了。于是,单枪匹马,独自启动了《河洛大鼓志》的编纂工程。
这些年自以为积累这方面的资料够多了,掌握的信息够丰富了,可临到用时方恨少。撰写《河洛大鼓志》涉及方方面面,千头万绪,都得一一查证落实。恨分身乏术,瞻前不能顾后,挂一难免漏万。一口吃不了个蒸馍,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在编撰上采取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先分后合的策略。所谓先易后难,就是从掌握得最多,最了解、熟悉,最好写的内容入手,把难啃的骨头放在后面,这样见效快,容易出成果。先简后繁也就是先粗后细,先把梗概框架简单粗略地勾勒出来,然后根据查找到的资料做进一步的细化、打磨。先分后合即每个章节的内容相对独立,各编各的,待完成后再并入总志。大部分章节都不是一气呵成,往往一边查找资料,一边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遇着磕绊,打住了车,就暂且搁置,搞其它的,待障碍清除了再回头继续。就这样,走走看看,写写停停,断断续续,添添去去,修修改改,缝缝补补,《河洛大鼓志》的初稿终于出笼。
有的笑啦,听你这一说,写志也挺轻松,挺顺溜,挺快的嘛。我去!说着容易做着难!说话一笔带过,够我忙活数载。不算此前几年做足的前戏,自2013年初开始着手动笔,至2015底初稿告成,足足超过了一千天,折合几年你们先算算!
三年里,除了必要的生存饭碗要端,余下的所有时间,扎进书稿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书本翻烂,网络踏遍,鼠标更换,键盘磨穿,QQ用爆,话费超限……厌烦时不禁自问,这是何苦,到底图个啥?哪个囟球愿做这出力不讨好的事儿?再一想,染下这个手,做下这缸醋,揽下这破事儿,总不能有始无终,编筐儿不收沿儿,做事不拾底儿吧?每想到此,把一怒摔下的键盘拣起来,让它重新服役;把扔到墙角的电老鼠重新“逮”回,继续为我效劳。
当然,说是独立完成一部《河洛大鼓志》未免有些言过其实,怎么可能呢?怎么可以把别人的付出都归功到自己身上呢?事实上,编撰《河洛大鼓志》并不是闭门造车,关住门一个人在屋里完成的。所有的文字并不是我肚里生出的,来自哪?来自网络,来自参考书籍,来自艺人之口,来自洛阳非遗中心邮箱的相关资料,来自……我只不过是梳理、提炼、排队、归类、组合,去伪存真而已。没有这些来源,哪来的《河洛大鼓志》?其中,电话采访求教过:巩义的尚继业、牛会玲老师,登封的郝总善、马贵民老师,偃师的张怀生、李明治老师,新安的王管子、王新章老师,宜阳的魏要听、王玉功老师,孟津的李小五、杜子京老师……这些都是在本地域比较有影响,有代表性,且对河洛大鼓知道得较多又比较热心的资深同行。他们大多都是有问必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有他们尽可能的帮助,《河洛大鼓志》从何谈起?嵩县的党俊乐,小伙虽然年轻,对本县曲艺界却了如指掌,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汝阳文化馆的潘红团老师,把自己八十年代撰写的汝阳县曲艺志资料无私奉献,让我几乎不动一枪一刀地借用了过来。洋洋《河洛大鼓志》里,同样融入了他们的心血和劳动成果,岂敢独专?
有衣无帽,不成一套儿;有志无序,难成体例。序居全志之首,志书之领,其重要位置不言而喻。序言的分量直接影响着志书的权重。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戏剧曲艺界之元老,河南省原曲艺研究会会长,德高望重的马紫晨先生为本志赐序,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
一切完工,就差最后出版的环节。这才想起,和金红之间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当初说过,审校、出版的事儿交由她。现在该指望、动用她的人际关系来走完最后一步棋了。可能原来没说得太明白。金红说过出版的事儿她办理,是因为认识有出版行业的朋友,出版没问题,但是费用是另外一回事儿。金红说,出版的费用嘛,我回洛阳找找几个朋友,看能不能把钱凑出来。当然,这需要时间和过程。
虽然金红在张罗这事儿,但我不想孤注一掷,打算两手准备,双管齐下。想起当初续谱活动发起时洛阳市非遗中心的赵博主任好像说过,必要时非遗中心会出手相助。如今到了必要的时候了,何不一试?
通过QQ群加了洛阳市非遗中心办公室主任李晓霞的QQ,提及了这事儿。李主任很感兴趣,她说:“我们非遗中心正打算出一本河洛大鼓方面的书哩,你提供的书稿真是及时雨。明天就向领导汇报。”次日报喜:“领导同意了,计划近日邀请你携带书稿来非遗中心一趟,专门召开个座谈会,研究出版的具体事宜。”又过了几个“近日”,却不见回信儿,忍不住发问,李主任这才回复:“哎呀,吕老师,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情况有变。领导说了,现在专项保护资金正在投入河洛大鼓数据库建设,没有多余资金,出书的事儿只能延后,等明年下批资金吧。吕老师,真的对不起!”嘿,一句话,晃啦。过了很长时间,又问:李主任,建的河洛大鼓数据库呢?答:不就是刚上线的那个“河洛大鼓官网”?呵呵,做了多年网站,还不知道网站就是数据库。后来留意到,这个花费数万元建造的所谓河洛大鼓数据库网站存活不到一年,便夭折了。当然这是题外话。
随常龙河洛大鼓演艺公司赴新乡参加河师大非遗月活动,结识了音乐系教授吉莉博士,多有QQ往来交流,谈及《河洛大鼓志》遭遇出版瓶颈。吉莉老师说可以帮忙出版。原来他们学校几个教授、老师评职称晋级需要出版有专著。自己写书费时费力效果还不一定好,借鸡生蛋不失为一条捷径。也就是说,《河洛大鼓志》的所有出版经费她们承担,条件是作者中必须附上出资者的名字。这样,我可以不花一分钱出书,她们可以此满足评职称的要求。可谓各取所需,皆大欢喜。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经历,不用说得那么清楚,也心知肚明。这么大的一部《河洛大鼓志》,多出几个作者无可厚非。反正我也不指望这评职称,转让给所需者,也是好事一件嘛。再说有几位高职称的大学美女教授加盟,也无形中增强了书的权威性。无论自己的身价,还是书的身价都有了提升。说起来这部《河洛大鼓志》可不是农民泥腿子写出来的,是专家学者的大作呀!有了第一次出版《河洛大鼓》的教训,这次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多少作者,我都是排在前面为第一作者,这个很重要,也是底线。对方不在乎排名第几,只要作者中出现名字即可。于是,很快达成协议,由吉莉老师联系中州古籍出版社,进入出版程序。
这次出书,好比孕妇生孩子,反正不是第一胎了,远没有首次出版《河洛大鼓》时的兴奋、企盼和急不可耐的焦虑。以平常心视之,顺其自然,瓜熟蒂落,十月怀胎期满,自会呱呱坠地。
这次出书按班就序、顺风顺水,从签合同到选题,再到申请书号,三审三校,最后付印,没有曲折和节外生枝,毫无磕拌。从交付出版到成书,前后只用了半年时间。2016年9月,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河洛大鼓志》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河洛大鼓志》封面封底

刚拆封的《河洛大鼓志》
[1] 搊:河洛方言,音(凑coù)。将人或物向上托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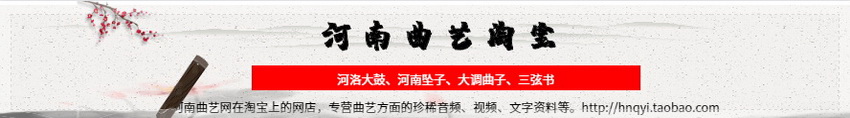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