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十四
刘黄说书遇老冯
望古垛说书结束后,继续北进,翻骆岭,下刘沟,越驼腰,至刘黄。
刘黄村是由明洪武初刘氏始祖刘八(名字失传,行次居八,故后人称“刘八”)从山西洪洞徙此荒岺,辟田营宅,从事农桑,繁衍生息。因多为黄土,故称“刘黄岺”,后简称“刘黄”,又以姓氏行次称“刘八岭”,乡下人往往会把地名念转音,叫“刘八两”。
在新安县大山以下,说起刘黄村,知道的人不多,但如果说起刘八岭,方圆百里几乎无不不知, 无人不晓。刘八岭之所以远近闻各,是因为村里出了个“大人物”叫王之波,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据说回刘八岭探亲时,从新安县城至老家沿途戒严,警卫排,吉普车排开数里,省县级干部前呼后拥。其地位显赫可见一斑。刘黄村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刘黄学校有着辉煌、悠久的历史,培养出许多出名的革命进步人士,出过韩钧、刘少力、王天新、高景川等有名的“大人物头儿”、“大杰士”。不仅刘黄村引以为豪,更是新安县甚至河南省的骄傲。
在如此有名望,有影响力的大村说书,如果能打得出,也是令人倍感荣耀的事儿。但我们却选择了“经过刘黄而不入”。郭汉老师说,如果说望古垛是大村,书不好说,生意不好做的话,但比起刘八岭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刘八岭很繁华,净出些“大干家儿”,文化人,能人更多,书更难说,事更难弄。没有两把棕刷子,还真不敢揽这漆器活儿。郭汉老师又说,俺掌柜(王管子)干了几十年,恁出名,在新安县大山以下各村各店儿,大沟小
旮旯几乎转遍了,就是没在刘八岭说过书。不是不想说,而是没机会,攥了几回劲儿,事儿都没弄成。可见这个村的书好不好说?
听郭汉这一介绍,我们都泄了气。人家王管子恁大的干家儿,恁大的名气,到这都打不出,咱们还是知难而退吧。不料郭汉老师话锋一转,又改变了口气:“球!我都不信这刘八岭的头就恁难剃?俺掌柜剃不了,不见得咱们也剃不了。再难剃的头也得剃,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猴不钻圈多敲锣。咱得想想办法嘛。”接着郭汉就说出了他的打算。
望古垛之所以能说(书)十八天,得益于找到了一个好“牌官儿”。但刘八岭郭汉从来不曾打过交道,没有熟人,不托底儿,找“牌官儿”无从谈起,如猫逮刺猥,无处下口。只有从周围入手,慢慢攻破。就像毛主席他老人家“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部署一样,先从附近的小村入手,渐渐向大村浸透。只要在刘八岭附近书说响了,扩大了影响,打开了局面,就不愁拿不下这块可望不可及的“阵地”。
一个失目的不识字人有如此的谋略和布局,让我们自叹弗如。怪不得人们说,瞎能!不无道理。常听有人背后议论:汉儿的眼就不敢能看见,要是能看见,说书可不是他的量儿,肯定是大干部角色,是弄大事儿人。一打交道,方知此言不谬也。
王河清说:“汉儿,这盘棋咋下,下一步咋走,俺们都听着你。你指东俺们不往西;你叫俺们坐,俺们不敢立;你叫俺们打狗,俺们决不撵鸡。”瞎,三句话不离本行,说书词也用上啦。
郭汉发话:“不进村,往西,今天的拐棍就靠到后罗沟的门上啦。”
罗沟是刘八岭西北方向的一道山沟,分前罗沟和后罗沟,同属刘黄大队管辖。后罗沟居沟底,翻道岭下去就是漏明河,是蜷缩在刘八岭以西最偏僻的一个生产队。
郭汉之所以选择这个偏僻的,不起眼的小村,用他的话说,那里是他和王管子老师的“老根据地”说过多次书,都是老熟人,老关系啦,人熟好办事嘛。
后罗沟距刘八岭三四里路,不知不觉就到了。赶得好不如赶得巧,进得村打听队长家在哪里,偏偏就问着了队长。队长四五十岁的年纪,刚装上满满的一架子车粪,正打算往地里送哩,被我们撞了个正着。因为是熟人,队长也不好意思指山卖路了,熟不忌礼,就和郭汉毛捣起来:“汉儿,又来都球哩!俺不说书,爬几巴走吧。”
郭汉也不饶人,笑着回奉:“说球哩怪美!就是不走。不说(书)也得说。今晚上没地方睡,就跟嫂子睡。”
队长摊摊手:“伙计,你看不见,也不管忙闲。没看看我正拉粪哩,哪有功夫照护你?”
郭汉挥挥手:“不要紧,伙计,我眼看不见,给你帮不上忙,俺徒弟眼治事着哩,叫他给你照护着拉粪。”又转向我下命令,“武成,去,给队长帮一下忙!”
唉,老师动动嘴,徒弟跑跑腿。尽管队长再三表示“不用,不用”,还是得硬着头皮,放下行李,跟在架子车后帮忙推车。先是推上了一道小岭,然后开始下坡。
我们老家的山路已经够坏了,无非是又窄又陡,转弯抹角,上山下岭地不好走,但好歹是土路,路面比较平整些。从没有见过如此糟糕的山路,看见都有些害怕。哪里象路?分明是一个石坎儿,一个石坑,大石、小石,小如拳头大如升,石挨石,石摞石,石套石,石头聚会,石头站队,石头打架,石头扎堆……,说是路,看不到路的形状,不见一点土,这才是山路,正儿八经的石路哈。
架子车下坡儿,车轮下面的石头好像变成了滚珠,车子的速度、方向特别不好掌握。按说架子车下坡,我得到车子前面帮驾车的端住车把,来控制下坡时强大的冲击和惯性。但看见这样的路,倒抽一口凉气,吓得腿都软了。队长也看出我不行,就说,不用来前面,在后边踩紧车尾巴就中。我如获大赦一般,赶紧老老实实地踩好车尾巴,两手使劲地抓牢车帮,以免被甩飞。架子车东摇西晃,忽高忽低,跳舞般地往下冲,差点把后面的人给撂起来,感觉幸亏各部位零件结实,不然非得撂散架不可。心里埋怨,郭老师呀,郭老师,你说句话怪轻巧,可把人折腾得够呛。
虽然不知是累的,还是吓的,出了一身臭汗,但效果还是明显的,力没有白出,汗没有白流。队长很痛快地将说书的事儿答应下来,一说(书)就是五天!我也落个“小伙儿书说得好,人也勤快”的好名声,甚至还有好心的大嫂子们打听、张罗着给说媒哩。细想想,出点力回报还是蛮丰厚哈。
酒香不怕巷子深。尽管后罗沟偏僻,信息闭塞,但“后罗沟来了一摊儿好说书的”事儿,一股名声,很快就传到刘八岭了。一传十,十传百,逢一加二,加油添醋,声势越传越大,神乎其神。有的说,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说家儿,听着美得很!那个讲,都说王管子说哩美,这说书的可比王管子强得多。
三传两传的,刘八岭人坐不住了,就有几个爱听说书,爱管闲事儿的凑一块议论:人家后罗沟都能说起书,咱恁大个村儿就说不起?撺掇撺掇队长,把说书的弄来说个月而四十的。
撺掇的人多了,队长们的耳朵也软了,心也活了,就说,说书是大家的事儿,只要大家都想听,那就说(书)呗。反正花的是大家的钱儿,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恰巧后罗沟队长去大队开会,和所有的队长碰到了一块儿。当大家问及说书的事儿,更是吹得天花乱坠,书说得如何好,听着如何美地喷了一通。几个队长当场表态:说(书)完言一声,接到刘八岭村里说。后罗沟队长就趁机把话砸死:既然想说,那就挨置好,哪个队开头,哪个队后续,哪个队收尾,一个队说(书)几天,定住了就不能反悔。男子大丈夫,说出话掉地下砸个坑,说啥是啥,说一不二。不能像妇女家一样,蹲那尿一泡,说话不算话。别到时候说书的来了,这个推那个的,推来推去的推黄啦。说书人统能着哩,得罪了他们,到处编排成书帽出息咱,可丢了咱刘八岭的名声啊。
几个队长不服气地怼罗沟队长:少露能!你罗沟能说起书,俺们刘八岭不比你的腰细。放心吧,通过开会这个公开场合决定的事儿,咋会滚瓜[1]?不行咱现在就开始排号。
大队支书见状说,既然是这样啦,我做主,给你们挨置。不说其它小自然村,单刘八岭正村有七个生产队,南一、南二、上东、上西、下东、下西、庙上。当即拍板定音,从东往西排,庙上队开始,以此类推,每个队三天。
一切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一切按照郭汉老师事先胸有成竹的预见和部署,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联系刘八岭说书,我们没有跑过一次腿,说过一句话,硬凭着说书的影响力和 “众人捡柴火焰高”的鼎力支持,顺利入驻刘八岭,打破了刘八岭历来“书难说,戏难唱”的壁垒。也更加佩服郭汉粗中有细,运筹帷幄的谋略和胆识。
刘八岭不愧为知名度极高的大村,自是和小村有着不一样的气质、气派。
那个年代,后山不通电,农村晚上说书一般都是桌子上放一个煤油灯,或从煤矿上使用烧柴油的“穿灯”。把灯头儿挑得大大的,为的是照的地方更大,更明。一晚上熏下来,大家不是黑眼窝,就是黑耳朵,黑鼻孔,一不小心再捏个黑鼻圪塔,清早起来吐口痰也带着黑丝丝儿。点两支蜡烛会环保很多,几乎没有油烟,但老是贵,一晚上得好几支,太浪费了,一般人哪舍得点呀。比较讲究,有条件的会在桌子上放一个老师批发作业用的带罩子煤浮灯,油烟少且亮。再气派的就是在书场悬挂一盏大马灯(桅灯),已经是比较上档次了。人家刘八岭牛得很,竟然在书场挂上了农村少有的,只有在乡镇唱大戏才能用到的汽灯!
天还没黑,庙上队长委派支应说书的几个人已经开始在刘黄学校门前的操场上张罗着忙活了,把桌椅板凳拉齐,烟茶备好,然后开始给汽灯换上一个崭新的石棉网罩儿,油添得满满的,气打得足足的,灯点得亮亮的,然后挂得高高的。人家大村对说书的重视程度,场面的隆重,也是其它小村所不及的。
按正常情况下,每天晚上开书前,尤其是刚到一个新地方的头一天,头一场书。因为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来说书的了,所以说书人早早赶到书场,先敲一通鼓,让四周的人听到鼓声,好来听说书,谓之“叫人”。但刘八岭就是与众不同,听众的热情高涨得让人意想不到。
当我们吃罢晚饭,早早地赶到说书地点时,乖乖,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学校门前的操场上,锃亮的汽油灯下,早已聚满了黑压压的一片人。丝毫不亚于唱大戏、开大会的热闹场面,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以至于我们来到人群外边,由于人太多,太过拥挤,我们竟然无法挤进到说书桌前。多亏照护我们的人在前面为我们开路,连喊带吆喝,连拉带推,左右开弓,硬是开辟出一道“人胡同”,才让我们费力地挤到桌前,前面走过,后面“人胡同”立即闭合。
四周都是人,挤得桌子差点被拱了起来,哪有说书人的立足之地?照护我们的又赶紧维持秩序,喝斥小孩儿们往后退,实在不行就下硬手往后边推。费了半天劲,总算是给我们打开了些场面,勉强腾出了说书人站的位置和拉弦者坐的位置。说书人坐的椅子不用装靠背,因为后面的人紧紧挤着,形成了一道天然舒适的“人肉靠背”。
如此规模庞大、混乱的说书场面,是我第一次见到,紧张之余,也有些激情豪迈之感。有的问,人这样多,会不会怯场?早就说过,我是“人来疯”。人越多,越来劲儿,精神头儿越足,发挥得越好。至于王河清老师呢,人家干得多了,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经过?更是临场不乱,镇静自若得“胜似闲庭信步”。等我垫罢场,定好弦,王河清不慌不忙归主正位。也不知他用的是什么魔法,只晃两下钢板,敲一声鼓,骚动的书场,喧闹的人群立即神奇般地静了下来。接着清了清嗓子,吟一首定场诗,道几句开场白,在清脆、柔和,泉水叮咚般的坠胡声中缓缓开唱。
王河清的腔很特殊,定弦很低。用艺人们的土话说,就是“不吃弦”,只能吃二分弦。啥叫“二分弦”呢?旧时艺人们好多不懂谱子,也不知C调、D调、E、F、G、A、B调什么的,也没有校音器啥的,定弦时用的是土办法,把C调的1、2、3、4、5、6、7、ⅰ八个音阶分别叫“一分弦,二分弦……最高七分弦、八分弦。象王河清定的二分弦等于简谱中C调的“2”音,相当低的。虽然吃弦低,但音域却相当宽宏,听起来来非常响亮。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一千多人的书场,即使站到最后边,最远处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王河清老师有文化,书词比较讲究,且吐字清晰,道白富有磁性,唱腔浑厚、明亮、圆润,有韵味儿。表演悠然自得,风度潇洒。说到入情处,全场鸦雀无声,屏心静气,似乎针掉地下都能听见;唱至热闹间,观众纷纷叫好,鼓掌喝彩,得稍微停顿一下,掌声、喝彩声才能平息。看着王河清老师出尽了风头,神气活现的演绎,听众如痴如醉的表情,弄得我和郭汉都有点羡慕和嫉妒了。
自然而然,我们说书在刘八岭打响了,比望古垛还要走红,生意兴旺的同时,在充满着一片恭维的赞叹声中,也获得了满满的成就感。
新安县大山以下大部分地区农村说书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说书一天两开书。怎么叫两开书呢。就是一天说两场,晚上一场是正身,一般说唱三板书,三个小时左右,下午加一场,不按正场,算奉送的,一般两个小时左右。既然不是正场,就不会开大书,主要说一些家长理短的孝道段,劝家书等,主要照顾一些上了年岁,行动不便,晚上不能来听书的老年人。也有一些听众要求接续晚上的大书,说书人就会耐心地解释:白天和晚上的听众层次不一样,白天听的晚上不一定听,相反晚上听过的,白天有事儿也不一定来,所以不能接续。说书人常唱:一人难趁十人意,一面墙难挡八面风。当然,听众大多数都是明事理的,不会强人所难。
那天下午,郭汉正在鼻子一把泪一把地唱着《接荆芭》,当唱到严永发用荆芭载着老娘,“拉到高山喂狼八”时,老娘细数养儿十月怀胎之苦,如泣如诉,唱至动情处,声泪俱下。王河清老师的弦子细揉,慢滑,极力地营造出哀怨、伤感的氛围。下面的听众一片唏嘘之声,大嫂们把脸扭向一边,不忍直视;老婆们低着头,拾起绑在前襟上的手绢不住地抹眼泪;有几个十来岁,和小严鸡儿年龄相仿的小学生,也在不停地拿手揉有点泛红的鼻子。这时候,谁也没注意,我坐的板凳头上多了一位不速之客。
正当大家沉浸在悲伤的气氛中,陶醉在书情里,从外边不声不响地走进一人,不动声色一坐在我的板凳头上。大家都只顾听书,没有谁在乎书场多了一个人。我专心致志拉弦儿,目不转睛,直到弦子弓戳到人家膝盖了,才发现板凳上多了一位“同座儿”。赶紧不好意思地冲人家点点头,以示道歉。人家冲我微微一笑,算是打过招呼。趁机打量一下这位充满好奇、疑问,似乎“空降”一般的神秘人物。
来人地地道道的庄稼人打扮,甚至有点土气,黑袄、黑棉裤、黑靴,配上黑黑的手、脸。从额头上布满的皱纹和黑白间杂的乱发判断,不会年轻了,至少六十开外。整体给人一种饱经沧桑的猥琐、狼狈之感。 不禁脑子里在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此人是谁,干什么的?为什么这般“不认生”,招呼不打,大大咧咧地贸然闯入书场,仿佛进入自己家门一般,毫不客气地坐入拉弦的位置了?如此行动举止,不像陌生人,倒似老熟人,老相识一般。倏然脑海中滑过一人,莫非就是郭汉老师他们经常谈起的那个说书人老冯?
常常听到王新章、郭汉、王河清等老师们不止一次地说起过有关老冯的奇闻轶事。郭汉还时不时地伸长脖子,扯着嗓子学老冯又粗又嘶哑的唱腔调门儿,以此来出洋相,取笑和逗乐。以至于虽没见过老冯,却从老师们的嘴里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听老师说过,他的原名叫冯堆子。呵呵,这是我听到的名字,具体的字是不是这样写,无从知道。系新安县正村公社白墙大队簸箕岭人,十几岁就跟着新安县河洛大鼓名艺人王振松学说书,是一大帮弟子中学艺最早的“大徒弟”,一干就是数十载,一辈子。每到一处,人们都叫他“老冯”,至于名字,大多数人已经从不提及,甚至忘却了。新安县提及说书老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提起冯堆子,没有几个人认识的。
正在想着是不是老冯呢,乘郭汉老师道白,弦子停下来的空隙,此人朝我看了一眼,竟然不和我商量,也不经我同意,从我手里接过弦子,说是接,还不如说是抢、夺,并站起身来,冲我示意,意思是让我给他让位。出于礼貌,我立即客气地起身与他互换了位置。这倒好,不但武器被缴,岗位也失守了。
难堪、尴尬之余,不禁暗想:既然人家敢夺你的弦子,抢你的位置,说明你拉弦子的水平不行,人家看不中,要做示范给你看。没有金刚钻,敢揽磁器活儿?说明人家一定比你拉得强。今天遇到高人了!想到这里,心里释然,充满敬畏和期待。静观人家怎样表现,趁机多学习一些精细吧。
谁知待郭汉老师起唱,弦子开始伴奏,我欣赏了一会儿高手的演奏,不由得大跌眼镜——不过没戴,不然早掉地下摔碎了。原来他的拉弦水平和我相比,半斤对八两,不相上下,谦虚地说,甚至还不如我。我虽然不行,好歹还能溜上大部分的过门儿,他几乎没有溜上一个字儿,哪里是溜弦,分明是扰乱秩序。王河清老师看不见,但明显感觉出溜弦的异样,不断地拿眼往这边翻,意思是,武成,你的弦子咋突然变成这啦?
我忍住笑,又不好意思再去抢人家的弦子,那是不礼貌的行为。更进一步加深判断,这一定是老冯,没错!
听老师说过,老冯干了一辈子,装了一肚子的书,在新安、孟津一带的说书艺人里,都没有老冯会的东西多、书目全,被誉为“一肚子两肋把儿的书”。据说早已失传的,好多艺人都不会唱的冷僻书,稀里古怪的老古董,都能从老冯的肚子里扒出来。但也是为数不多的“单片子”,一条腿走路的艺人之一。啥叫“单片子”?就是会说不会拉,或者会拉不会说的艺人,叫“单片子”,也称“缺一门儿”,行内称为“一条腿儿走路”。也就是老冯书说得好,道行深,但不会拉弦儿。今天一看,这个人拉这两下根本称不起会拉弦儿,不是老冯还能是谁?
老师又说过,老冯年轻时,嗓子很好,书说得很漂亮,走南闯北,声名远扬。方圆百里,老冯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啜子坏了,坏得不可收拾。从此后,嗓音变得越来越难听,张大嘴呵出来的声音,又直、又粗、又嘶哑,严复地影响了唱腔调门的发挥。老冯也曾不止一次地调侃自己:“我这腔是‘破竹竿捣尿罐儿,噼哩噼啦地不好听’。”再后来,老冯的名气大跌,找他说书的越来越少。使他倍感落寞,颇有“一肚子东西倒不出来”的遗憾。
老冯没上过学,斗大字不识半升,很难想象 “一肚子的书”是怎么装进去的,我想与他过目不忘,听过一遍就能记住的超强记忆力有关吧。不但记性好,而且还能“吃荆条屙箩头,现编”。随机应变,临场发挥能力极强,很有些“就地取材,现打热卖”的本事。
有一个很广泛的传说:老冯说书路过北冶贾岭的九孔窑村,被好听说书的热心群众围住,要求先说一段听听,中啦,就找队长晚上说书。老冯就很卖力地唱了一阵子,说罢了被告知,队长没在家,去公社开会了,让他在这老等。一直到天快黑,才把队长等回。谁知老冯无论怎么求告,怎么死缠烂打,队长以队里没钱为由,死活不答应说书这回事儿。老冯又急又气,冲队长嚷道:“我白给你们送了一场书?群众叫等你回来,晚上好说书哩,这倒好,满大劲来一个满松劲儿,叫我白等这一下午咋说?”队长不买账,话怼了回去:“我叫你送书嘞?谁叫你送书,叫你等,你找谁去!给我说这些难听话做啥?赶紧走,不用在这碍事!”一句话,呛得老冯哑口无言,轻易被打发“滚蛋”了。
搭了一场书,又赔进去大半天功夫,临尾遭人驱逐,还落了一肚子气。事后老冯越想越觉得憋屈。一肚子死血没处放,于是就把这件事儿编成了一段书帽,在九孔窑附近到处唱:“九孔窑群众把我榷嗨,清早等到日头落,我说队长说一场,队长说,牛犊有病没钱抓药哎……”这个书帽唱得多了,小学生们也学会、记住了,就好像现在流行歌曲一样,到处传唱。传到了九孔窑人的耳朵里,感觉确实有些对不住人家,自知理亏,也无可奈何,只得感叹道:唉,啥人都能惹,千万别得罪说书的,编成书帽到处宣传,把咱的名声也丢尽了。
老冯说书不拘泥于书本上的死词儿,活学活用,把日常生活中生动有趣,极为家常化的语言,巧妙地融入到书里,让听书人感到象拉家常一样,亲切、自然。每到一处,很快就能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极受欢迎。但由于他太“水嘴[2]”,说笑话不知轻重,大大咧咧,过于随便,倒也为此吃了不少亏。
有一次在崔沟说书,白天没有事儿,和一个年轻的家庭妇女拉家常。问人家:“你娘家哪里?”对方回答:“司沟哩。”老冯说:“哎哟,司沟我去过,姓司的多,你姓啥?”对方笑笑:“我姓司。”老冯嘴不遮身,顺嘴流,瞎胡编的毛病又犯了,不由脱口而出:“哎,你姓撕(司),我姓缝(冯),给你撕开,叫我给你缝缝。”
如果人熟了,且年龄相仿的同代人,说这种笑话虽然过分一点,对方不太计较的话,倒也没啥。好不该老冯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头了,人家才二三十岁的年轻妇女,说这样的话就不是不讲方式的问题了,叫不会说话,为老不尊。搁农村说,就叫“没材料”,这种笑话是你这一大把年纪的人能说的吗?
果不出所料,人家年轻妇女不买账,沟里拾些禾,立马(挠)恼了上来,破口大骂:“去把你姐、你妹子、你闺女撕开缝缝去吧!”劈头盖脸地一顿骂,骂得老冯头真想往裤裆里扎,恨不得找地缝儿钻进去。招来围观者纷纷数落老冯的不是,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弄得老冯狼狈不堪,书不能再说了,已经说过的书钱也没法再要了,灰溜溜地卷铺盖离庙。一句笑话,得不偿失哈。
《拉荆芭》终于说完停了下来,老冯才得了机会,站起来拍了拍王河清的肩膀:“河清,架子真大啊。来了半天都不理我。”
王河清马上听出了老冯的声音,赶紧也站了起来:“哎呀,老冯,你咋来啦?”
按理说,他们两个是师兄师弟,一定十分亲近的。但除了见面时彼此寒暄几句外,好像再没有过多的话,可能是碍于书场公开场合,不宜过多交谈的原因吧。说了几句话,和郭汉打过招呼,不用等邀请,就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河清,汉儿,叫我说一段儿吧?”还没等郭汉点头,就走到桌子后边,把郭汉撵了起来,然后掂起了板。
记不得唱的是什么名称了,也没有听进去任何内容,只是耳的为虚,眼见为实,从现场切实感受到了老冯说书的特色。遗憾的是相见恨晚,未能领略到他年轻风华正茂之际,嗓子没坏之时,名噪新安、孟津,叱咤曲坛风云的风采了。再难看到那个在大山以下“一手捏俩麻知了,一捏两响”的老冯了。现场目睹老冯说书,真的替他难受,嗓子不是一般的坏,也不是一般的嘶哑。每唱一句,感觉到浑身都在使劲儿,整个身体弯得象一张弓,脸憋得通红,脖子憋得大粗,喉咙和气管已经扩张到最大限度,张大嘴憋出每一个字来,让人看着心疼,唏嘘不已。嗓子的嘶哑、混浊,已经严重影响了吐字、发音和演唱技巧,听起了就象人们常说的“老粗腔,老直嗓”,很多地方听不清楚,更别提婉转悠扬之美感了。以往郭汉模仿老冯的唱腔,出老冯的洋相和窝囊,跟现实版的老冯比较起来,还别说,真的有几分象啊。
一段书唱完了,观众没人鼓掌,我们仨出于礼貌和尊重,自己给自己人象征性地拍了几下手,让其就座。我赶紧将不热不凉的茶水递到老冯手上,客气地说:“冯老师,请喝茶。”老冯感激地双手接过茶缸,喝了一口,放在卓上,然后亲热地拍拍我的肩膀:“小伙子,弄得不错,年轻有为,好好学,以后能成大器。有哪段书不会,尽管问我。我肚子里东西多着哩,你学一辈子都学不完。唉,好汉不提当年勇,我老了,不中用了,嗓子也不争气,一肚子书没人学,死了带到棺材哩可惜呀。”
诸多年后,每想起老冯发自肺腑,语重心长的这段话,常顿足叹惜,悔恨连连。然后悔已晚,老冯已经真的,毫不客气地把一肚子的书,那可是现在好多艺人都不会,已成绝响的东西啊,一点不留地装进了棺材,带进了坟墓。以至我现在谈及此事,心中隐隐作疼,却又无可奈何。
可惜当时年少无知,年轻气盛,不以为然,对老冯这番话阳奉阴违,明里唯唯诺诺,暗中嗤之以鼻。心里好笑:看你老冯说这书是啥东西,难听死了,还当成宝贝哩,谁稀罕你一肚子的烂杂碎!白给我也不要!
说实话,当时真不看好老冯的书,老粗声,老直腔,哑喉咙倒不说,唱词也太土,土得掉渣,上不了台面,登不了大雅之堂。那时我刚出学门,自以为识了几个字,心性狂傲,好高骛远,热衷于追求什么高雅,对这老冯的这一套俗不可耐的“过时货”不屑一顾。直到八几年后听到了偃师河洛大鼓艺人牛共禄的磁带《搬龙角》,感到无论其唱腔、调门、书词和老冯如出一辙。甚至相貌和演唱风格也惊人的相似。同样,我对牛共禄的书也不感冒,认为土里土气的,不讲究做派和仪表,距心目中的高雅艺术相去甚远。但牛共禄的《搬龙角》《竹林认母》等磁带很快风靡豫西,在那个盛行盒式录音机的年代,几乎家家户户都能飘出牛共禄的声音,有很多年轻人甚至能象模象样地模仿几句。
看到这么多人喜欢、痴迷于牛共禄这种风格的河洛大鼓,不得不使我改变初衷,重新审视这种粗犷的,不拘细节的,土里土气,充满泥土味的民间说唱艺术。恍然所悟,我所追求的所谓高雅艺术,是多么的孤芳自赏,曲高和寡,成了无根草。之所以老冯、牛共禄的书在农村如此受欢迎,喜闻乐见,是因为他们说的是地地道道农民化的语言,演绎的是平常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家长理短,最接地气,深深地植根于民间的缘故。
摸着枕头天已明了。当我领悟说书艺术真谛,发觉老冯“一肚子东西”的价值时,已经为时已晚。老冯走了,过那边儿说书了。刘八岭说书,见了老冯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从此永别。
几十年过去了,一切都成为过眼烟云。时间冲淡了一切,却无法把仅有一面之缘的老冯从记忆中抹掉,也时常惦记着他那“一肚子的东西”,然水中望月而已。
[1] 滚瓜:新安方言,说话不算数,反悔之意。
[2] 水嘴:新安方言,指说话过分随便,不讲方式,该说不该说的都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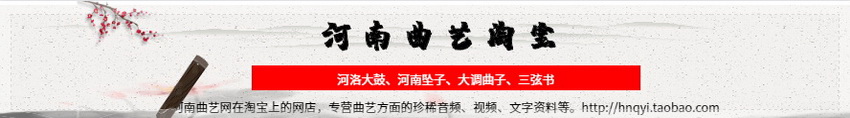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