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廿八

繁琐的家事儿,拮据的生活,能削弱人的意志,磨平人的棱角。艺术和生活是两码事儿:艺术是崇高的、浪漫的、高雅的境界,生活却是平淡的,乏味的,严酷的现实;艺术可陶冶自己,娱乐别人,是虚幻的,朦胧的理想,而生活却是柴米油盐,衣食饱暖,赤裸裸的现实。有时候,人的理想、爱好和追求不得不向生活低头、让步,甚至投降。
八五年春,家里事儿太多、太杂,钱的去路比比皆是,钱的来路捉襟见肘。凭说书挣那俩钱实在经不住花。往往是寅吃卯粮,这一季透支的是下一季的花销。一是为了摆脱困境,二是确实有些棘手的事羁绊,无法出门。只好先把说书放一放,到竹园下坂峪山上的元家庄矿下井干活。说白了,还是前面所说的“进窑”,不过这时候硫磺矿的井下作业比原来条件好多了,通上了电,也不再“拉小筐”,总之,干一段时间,也是可以适应的。
在矿上干了一春,手上小有积蓄,底气也就硬了起来,潜伏在内心深处的说书念头又开始蠢蠢欲动了。麦刚刚收罢,憋了几个月的喉咙又痒了,着急想说几天书发泄发泄。正愁想出去说书没人搭班时,孟津的杜子京摸上门来。
早在初学徒时,就不止一次地听王老师和郭汉老师提起过杜子京。其间仅会过一面,我见过他,他却没见过我。为啥?他看不见呀,头碰头也见不了我,况且只是见一面而已,连个招呼也没打。虽没打过交道,但从老师们嘴里,有关杜子京的事儿也了解得不少。看得出,不论是王老师,还是郭汉和王河清老师提起杜子京都很讨厌的样子,每次在路上碰见,或摸到门上时,都是躲躲闪闪的避而不见。
杜子京,孟津横水元庄大队核桃树坪人。属虎的,比我大一岁,却早学了三四年,资质相对比较老些。据说他以拉弦为主,行艺经历比较丰富,新安、孟津好多知名的河洛大鼓艺人都给人家搭过班,拉过弦儿,但都是“坐不稳,暖不热,三天不到就散伙儿”,所以一直没有固定的搭档。行内人都说他是土桥说书艺人张抓子的徒弟,但他不承认这个老师,说只是在一块厮跟过,怎么就成徒弟了?据他自己说,是跟横水街老艺人畅朝学的。后来才明白,之所以不想承认张抓子是他的老师,是嫌弃张抓子技艺水平太低。在新安、孟津河洛大鼓届一直流行着“新安县数着[①]吉会子,孟津县数着张抓子”的说法。这里的“数着”不是正数第一,而是倒数第一。换句话说,他两位是新孟一带最不咋着的说家儿。杜子京摊上这样的既没水平,又其貌不扬的老师,感觉把自己也拉到稀泥沟啦,跟着丢人,不想承认也在情理之中。攀上孟津比较有名气的河洛大鼓第三代艺人畅朝作为老师,自己的名气和地位都提高了不少,更重要的是爬到了高枝上,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成了河洛大鼓第四代艺人,和新安县的王管子、郭黑蛋、姜治民,以及孟津县的韩朝渊、李小五、杨保险、乔新甲等“好说家儿”平起平坐,生生地比俺老师王新章、郭汉还高了一辈儿。
早上锄了一晌玉黍地,还没来得及吃晌午饭,就是几个半大娃们,侄哩侄,孙哩孙的,跑到家中报信儿,有的喊叔,有的喊爷:“快点儿,说书的王管子寻你来啦——”
我纳闷,王管子是“大干家儿”,“名说家儿”,只有我去拜访人家的份儿,哪会摸到咱这“无名小辈儿”的门上?于是大声地呵斥他们:“去,去,去,都爬得远远的!哪来的王管子?”
话没落点儿,就听院墙外面有人高声喊着:“武成——,在家没有(促读miáo)?”声音没落,一个身材矮胖,肥头大耳的盲者,背着弦子,一手执一根长竹棍儿,一手被一小孩儿拉着,已经进了院子。
怪不得小孩儿们都说是王管子来了,还别说,杜子京的相貌还真有些相似。都是体态很胖,方脸浓眉,两耳坠肩的,说话的声音、语气,走路的姿势都有点像王管子。杜子京长得像王管子,并很崇拜,和王管子搭过班,自然也会刻意地去模仿他的一言一行,甚至包括说书的唱腔、调门等,俨然成了“小王管子”。但言谈举止和气质比起王管子来,还是逊色了不少。体型虽像,却没有王管子的魁梧高大;唱腔虽模仿王管子的浑厚,却不及其宽宏、嘹亮;书场上一站,虽有点王管子的架势,但威风和魄力逊色了不少。总之,杜子京比王管子低些,胖些,年轻些,举手投足迟钝些,行动拙笨些,还是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的。

尽管我们仅一面之交,连腔都没搭过,但杜子京喊我名字的声音和语气,进门的大大咧咧,一点都不生疏,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老相识似的,显得非常亲热、随便和自信。
有同行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虽说不很熟识,但毕竟人不亲行亲,人家热情地摸上门来,得尽地主之谊。况且正想瞌睡,有人递个枕头。正愁出门说书没有搭档,有同行找上门来,岂不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自然是迎进家门,热情招待了。
不再说杜子京出门跑得多,老江湖了,嘴边儿的挂面子话、奉承话一套一套的。尽管没有任何交往和感情,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武成,我老想你呀。”听着麻麻的,酸不溜丢的,但很受用。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了“我老想你”这句口头禅,发现他不管见了谁,都是这句客套话。就像冯巩每年春晚和观众见面时的第一句话“我想死你们啦”,还没等他开口,观众已经替他说了。
当然杜子京套近乎的本领还远远不止这些。我们还没说上几句,他就又开始恭维起来:“武成,你这人老美呀,腔美,书说得也美,咱们老对脾气呀!今年夏天说啥也得厮跟厮跟。”
对于这套恭维话,我不置可否地笑笑,这高帽儿戴得也太不靠谱了吧。根本就没有听过我说书,咋就知道腔美,书说得美?初次见面,没有在一块儿共过事,搁过伙儿,咋就了解我这人“老美”,“老对脾气”呢?这马屁拍得,拍着拍着都拍到马蹄子了,还要往下拍哈。
赶上“饭点儿”了,我嗯嗯啊啊地应诺着,安置他坐好,张罗着去端饭,杜子京问:“啥饭?”我说:“家常便饭,小米稀汤甜面叶儿就花糕馍。”他喃喃地说:“哎哟,我不想喝汤吃馍,好吃捞面条。那你们吃吧,我不饥。”言外之意,就是想让做“改样儿饭”,给他另外擀面条吃。我心中有几分不悦,像我们说书跑江湖的,踩百家门儿,吃百家饭,厨艺有高有低,茶饭有好有赖,口味有咸有淡,要适应各种各样的饭食,最忌讳的就是挑食、拣饭,这不好,那不吃地难说话,难侍候。如果人熟识了,熟不拘礼,在主家乐意的时候,说出想吃啥饭的意愿也未尝不可。但初次见面,人生面不熟的,就贸然“点饭”给人增添麻烦最为不好。
初次认识,碍于面子,嘴上不好说啥,仍然把饭菜端上来,递到他的手里。谁知人家说不吃就是不吃,任凭怎样推让,坚辞不受。我说:“杜先儿,有点对不住啦。刚做罢饭,煤火用湿煤封住了,一时半会无法扎开火做饭。如果不吃,可要饿肚子了,将就着吃点吧。”杜子京仍固执地说:“没事儿,不饥,下一顿吃吧!”
吃不吃,让到,吃了吃球,不吃去球!心里不耐烦地想,没敢说出来。大老远摸来,赶上吃饭时候,我们吃,叫人家看,不论面子上或心里都觉得过意不去。连基本的待客之道都没有,更提不上热情招待啦。唉,人家不吃,咱有啥办法?
按照惯例,同行见了面,除了寒暄,少不得拉拉唱唱。饭不吃,但书得说,弦子得拉。况且已经闻讯聚来一些邻居,起哄让来一段儿。我说:“杜先儿,你看大家都来了,想听哩,要不咱就来一段儿?”
杜子京慢吞吞地说:“中嘛,咋不中?又不是外人,肯定得说(书)呀。”
我赶紧张罗着拉桌子,搬板凳,鼓支上,钢板、鼓槌摆停当,才请杜子京就位:“杜先儿,你是远道而来的客哩,请坐上位,先给大家说一段儿吧。”
杜子京也很客气:“哎,吕先儿,我大老远地来,就是想听你说书哩,你先来吧。”
我说:“杜先儿,俺们都是左邻右舍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我这两下子他们听过来,听过去的,已经絮烦,不稀罕啦。常言说得好,外地和尚会念经,都想听杜先儿给大家念个好‘经’呢。大家说,是不是?”
大伙儿跟着起哄:“对,先叫人家老师儿王管子来一段儿,大家拍拍手。”
农村人把鼓掌说成了“拍手”。有人提议,就跟着响起了一些稀稀拉拉的掌声。我赶紧更正:“你们认错人啦,这可不是王管子啦。这位老师姓杜……”
有人说:“不是王管子,肯定也是他的徒弟,不然咋会长得真像哩。王管子是好说家儿,徒弟说得也不会赖。说一段听听!”
无论怎么邀请,大伙儿怎么将[②],杜子京说啥也不肯先说(书),推让了一番,我只好扶他入座拉弦的位置。
或许他看不见,做事多有困难;或许他体态太胖,行动诸多不便。杜子京给人总体的感觉就是一个“慢”字,慢腾腾地走路,慢吞吞地说话,慢悠悠地落座,慢慢地掏弦子,细条慢理地定弦……总之,慢得让人沉不住气。
王老师他们不止一次地数落过我脾气大[③],做事没有紧慢,拖拖拉拉,但和杜子京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我一切准备停当,拿起了钢板,掂起来鼓槌准备开唱了,这边儿杜子京的弦子吱吱呀呀地还没定好。我有些耐不住性儿,等不及了,又不好意思当众明着催促,就有意识地摇两下板,敲两声鼓。这是我们河洛大鼓行当中约定俗成的“暗号”。相当于戏曲中的“叫簧”,意思是告诉拉弦的,已经准备好,要开书了。当然,明眼人可以打个手势,试个眼色,失目人看不见,只能通过打鼓击板来“递簧”。这种催促无效,人家虽然不 “视而不见”,却也是充耳不闻,根本不理睬这回事儿,仍然是不紧不慢,磨磨蹭蹭。算啦,不管他啦,我连续击鼓打板,打了个“富贵不断头”,没打几下,杜子京的弦子迅速跟了上来,拉了一段儿“小鼓头儿”。
按照约定俗成的说书路数,河洛大鼓在农村地摊儿开书前,一般都要来一段儿前奏曲,叫“鼓头儿”。一来起到叫人、招徕听众的作用,二来可以展示拉弦技艺,乐队实力。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弦子拉得好坏,亮出来让大家瞧瞧。“鼓头儿”欢快、紧张、热烈,有势如破竹、急风骤雨之势,指法、弓法必须得娴熟、流利、灵活,是最能体现拉弦功底的。
“鼓头儿”是行内专业术语,音乐旋律大致和曲剧的十八板(有的称“十大板”“大起板”等)差不多。很难说清是曲剧的十八板借鉴了河洛大鼓的“鼓头儿”,还是河洛大鼓的“鼓头儿”引用了曲剧的十八板。随着河洛大鼓音乐的革新,实际上有的艺人在演奏“鼓头儿”时完全照搬了曲剧的十八板,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
“鼓头儿”也叫“闹台”“开场曲”,偃师、巩县一带也称“鼓扎”。“鼓扎”分“带丝儿鼓扎”和“干鼓扎”。江湖春点儿称弦子叫“丝儿”, 很显然“带丝儿鼓扎”就是一边击鼓打板,一边弦子演奏的“鼓头儿”。
根据演奏的时长,“鼓头儿”又分“大鼓头儿”和“小鼓头儿”。“大鼓头儿”用于每场书的开头,时间较长,大多十分钟以上;“小鼓头儿”用于每段书的开头,时间较短,一般不超过一分钟。从音乐结构看,小鼓头似乎是大鼓头的压缩和精简版,删去了开头缓慢的部分,直达高潮结尾。因小鼓头更加紧凑,更加矮小精悍,故也称“小摧板儿”。
杜子京行动迟缓,定弦拖拉,可一旦拉起弦来,便如打了一针速效兴奋剂,立马打起精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进入状态,让人始料不及,不禁为之一振。
早听说杜子京拉弦很有特色,不是一般的卖力,浑身带劲儿。耳听为虚,今日总算领教,开了眼界。说书的表演不足为奇,拉弦的带动作极为少见。从艺三四年,见过的拉家儿不少,大部分讲究坐姿端正,稳重大方,很少见摇头晃脑,浑身乱动的拉弦习惯。当然也有一些拉弦儿相当投入,肢体语言极为丰富的大师级别的高手。他们认为肢体语言是演奏技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肢体语言,艺术将大加折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
杜子京把演奏中的肢体语言发挥到极致。别看平时像一头老疲牛,死气沉沉,雷打不动的,弦子一响,便如睡醒的猛狮,不动则已,一动则惊人矣。不得不服气人家的功夫,指法、弓法相当地快,相当地猛烈,音符听起来跳跃性强,有力度。更重要的是他拉起弦来,不只是胳膊、手腕用力,而是浑身上下抖动,胳膊腿乱动弹,外加摇头晃脑,而这一切动作幅度相当大,相当夸张。乡下农村人把拉弦卖力,拉得劲大的称为“恨弦儿”。杜子京的“恨弦儿”不是一般地“恨”,抽起弓来似乎用尽全身之力,调动五脏六腑之功,咬着牙、张着嘴、翻着白眼儿,身子前倾后仰,脑袋左右狂摇,恨不得把弓拉直,把弦拉弯!由于过分肥胖,摇头晃脑的同时,感觉脸上的肌肉在狂颤、乱抖。
这一段“小催板儿”拉下来,不说拉得好坏,艺术效果如何,单是投入的面部表情,夸张的肢体动作已经把戏赢了。下面听众不多,却一片哗然,说不清是叫好、喝彩,还是嘲笑,兼而有之吧。
杜子京的拉弦风格早有耳闻,业内称之为“出古”,即出奇招、怪招,稀奇古怪之意。对这种“出古”,同行评价不一:新安县大平沟的河洛大鼓艺人狗刘子认为拉得美,叫好。因为戏曲丑角行当出身的狗刘子说书自身动作夸张,也爱出丑,耍过点儿,引人发笑,所以志趣爱好相投。而俺老师王新章比较刻板,爱循规蹈矩,对这种摇头晃脑,浑身乱动的拉法嗤之以鼻,认为是胡来,“脏弄家儿”,“贱病儿”。受俺老师的影响,我也不看好这种过分地张扬、做作,认为这是艺风不正。
不管咋说,杜子京的这种拉法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引起轰动的。就拿人家拉这一段儿,有几个听众交口称赞拉得好,有劲儿,不知是真心、由衷地好,还是碍于面子的奉承和恭维,反正是叫好了。
我做开场白:“既然杜先儿不愿意先说(书),那我就来一个抛砖引玉吧。老少爷们先听听咱自家人唱得赖的,然后再听老师儿唱得好的。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哩。大家沉住气不少打粮食哈。”唱了一段儿,下雨淋到当院,淋(轮)也淋(轮)到杜子京啦。杜子京也就不再推托,交了弦子,归了正位,一段“催板儿”奏过,开始作定场诗:“高高山上一棵蒿,不见同行心发焦。今日见了伙计的面,俺喝口凉水也上膘。”
大家听了哈哈一乐,感觉很新鲜,纷纷交头接耳称赞:“中,这说书的即兴发挥,现打热卖,吃荆条屙箩头,现编得还怪美哩。”我笑笑,心如明镜:这哪是现编的?这首定场诗虽然“不在书”,却也是无数代老艺人口口相传下来的,用于同行见面时的特定场景,不止一次地听别人说过,也早已了然于胸,并非杜子京的专利和独创,但下面听众哪知道这么多?
杜子京唱了一段《一文钱》,也叫《蓝老汉拾钱》。说的是一个吝啬老头拾到一文铜钱,不小心咽到肚子里,认为活不成了,叫三个儿子安排后事儿。嫌老大老二儿子办丧事太浪费,老三儿子是杀猪的,主张把他爹 “人肉当成猪肉卖,不下本金还赚钱”,反被老头看好。整个段子妙趣横生,忍俊不禁。也听王管子说过这段儿,不知是王管子学杜子京的,还是杜子京学王管子的,反正模仿的是王管子的唱腔和唱法。同拉弦子一样,他唱起书来,也相当“恨书”,气沉丹田,浑身带劲儿,善用“吞口儿”,重“吐字”,很有些王管子唱书的味道。但总觉得有些夸张,有些过了,吞口过实,咬字过重,听起来有些不自然,不舒适。艺人之间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唱法,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也不好作过多的评价。
杜子京头一次到别人家里,就显得非常熟识、随便的样子,太不拿自己当外人啦,为此闹了一些小小的不愉快。
不知从哪里听说俺媳妇的名字,就提着她的名字大声喊叫,一会儿喊让她舀水洗手洗脸哩,一会儿又喊着找针线补衣服哩,净成他的事儿啦,很让人感到厌烦。这都不是主要的,不管认识不认识,熟悉不熟悉,就随便地喊家庭妇女的名字,很让俺媳妇反感和不爽。
新安县大山以下的风俗比较封建,女性的名字在娘家当闺女时会常被人喊叫,一旦出嫁后,就很少人知道名字,更别提随便喊了,一般都称为“屋里人”,或“某某媳妇”。晚辈或平辈的不是称某婶、某娘、某奶、某嫂,就是称姑、姨、妗子等;长辈的则称为“某某家的”“某某屋里人”“某某他娘、他婶儿、他嫂……”。你想,同村的,一家的,熟得不能再熟的,尚不能随便提住名字喊,何况是陌生人?
当然杜子京也有人家的想法和道理,直呼其名更容易套近乎,显得亲近、家常,这也是人家每到一处,就能很快与当地人混熟,打成一片的处世经验。可俺媳妇比较内向、封建,墨守成规,不吃这一套。第一次喊名字装作听不见,第二次喊名字时生气不理,第三次喊名字时,就“沟里拾柴禾,恼(挠)上来了”,冲着杜子京发起了脾气:“这人咋这股劲哩!谁叫你喊我名哩?我的名字是叫你喊的?”
杜子京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很不自在,但也没恼,不卑不亢地笑着说:“咋,你的名字是在箱子里锁着哩,不敢喊?”
“就是不想叫你喊,谁认得你是哪根葱!”
杜子京被呛得嘴张了几张,白眼翻了几翻,一时说不出话来。我赶紧打圆场:“算啦,算啦,名儿喊喊怕啥?又喊不掉谱儿。去,去,赶快做饭去吧。”把俺媳妇支到厨房去了,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下来。
一时的气氛弄得很尴尬,我劝道:“杜先儿,别生气,不用跟屋里人一般见识哈。”
杜子京吃了个没趣,仍然显得很有肚量地笑笑:“没啥,不叫(让)喊就不喊呗,以后注意些就是。”
按理说,急着出去说书没有班儿,杜子京找上门来是好事儿,高兴还来不及呢。可当他再次提及合伙搭班的事儿,我却犹豫起来:一来初次见面,挑食、拖拉的毛病就有点看不惯,加上刚才闹的那场不愉快,过分随便,爱给人添麻烦更惹人讨厌,搁我们那里的方言土话说,叫“膈噫人”。二来和王老师他们分手后,已经三年没有照护过失目人了。清闲、利亮惯了,猛一下要照顾一个瞎子,给他领路,侍候吃喝拉撒,简直是自寻麻烦、不自在。侍候老师是份内之事儿,天经地义,无端侍候别人,没有那个义务,还真的有点不情愿。再说王老师、郭汉、王河清他们行动敏捷,也好照护,而眼前这个杜子京胖得拙笨无比,跟猪一样慢吞吞的,给他领路还不把人急死?
嫌毛病多,讨厌人,自己不想侍候瞎子……这些不想和杜子京搭班的理由只能留在肚子里,岂能说得出口?能说得出口的理由却变成了这样:“杜先儿,我也想跟你搭帮,一块儿出去说书。可是今年夏天种了两亩玉黍黍,一亩红薯,锄了头遍儿锄二遍儿,还得上化肥,老是忙,抽不开身,顾不着出去啊。等上冬闲了,咱俩再搁伙儿说书,你看咋样儿?”
老实人也有奸诈之处。虽然咱这个人性子直,不会拐弯儿,不好捣鬼,但偶尔也会口是心非,言不由衷一回,说瞎话、假话听起来好像跟真哩似的。有时说话办事要讲策略,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能讲真话的。总之,就是想个办法,找个借口,把杜子京给推托走,不知算不算“道不同,不相为谋”哈。可是,他后面说的一番话又让我蠢蠢欲动了。
杜子京虽然眼瞎,耳朵一点也不聋,心眼一点也不少,很明显地听出来“家里农活忙,出不去”是找的客观原因,于是就不慌不忙地说:“总不能在家锄一夏天地吧?咱们老对脾气,不厮跟老亏呀。咱这一带说书不中啦,生产队照不住头儿,不好联系,生意不多,挣不住钱。咱不在近处说(书),上东边儿巩县去吧。那边私人还口愿的神书可多啦,说一个神书三天,一家跟一家儿,接连不断。书价比咱这边高不说,封的‘礼儿’又大又多,三天神书,光‘封儿’下来,也比咱新安县这边正身书价还多。”
早就风言风语地听说过,巩县是“说书窝儿”,书多,价钱大,孟津好多比较出名的说家儿,像李玉山、李小五、陈振奎、张建波等,都跑巩县去了。耳听为虚,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到巩县“眼见为实”。今儿听杜子京一说,就有点动心了,试探着问:“杜先儿,你去过没有?就咱俩人中不中?到巩县那边能打得出不能?”
杜子京说:“我也没去过,但俺们孟津好多说家儿都在巩县说过书,包括老张,就是张抓子,你听说过这人吧?咱俩人都没去过,不摸底细,不知大头小尾,没多大把握。再说去那边说书得要证明哩,咱俩都没有。不过咱可以再找一个人,就是给你说的张抓子,他有文化馆开的证明,急着去巩县没有合适的班。正好趁他的证明,咱仨一块下巩县,硬扎扎的一班儿人马,到那里保准一只手抓俩马知了——一捏两响。到秋熟挣个一腰腰的票子回来,可比侍候你那两亩玉黍黍强得多啦。”
杜子京这一番话,让我彻底坐不住了,有点跃跃欲试。尽管从心里“膈噫”他的人品,不屑与瞎子为伍,但金无赤金,人无完人,尘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儿?权衡利弊,还是很干脆地答应下来。
话不啰嗦,说干就干,立即行动。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赶到横水公社的土桥大队,见了新孟一带以最不咋着出名的说家儿——张抓子,仨人一拍即合,做了一些简单的磨合和准备工作,装备齐毕,准备坐车到洛阳买票,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就在人马齐备,整装待发,准备东征之际,杜子京提出了一个赤裸裸的问题:“没出去之前,咱先商量一下,账咋分?”
我不以为然:“还没出门哩,一场书没说,一分钱没挣,就讨论咋‘分赃’哩,太早了吧?等挣下钱再说也不迟!”
杜子京说:“哎,先丑后不丑,免得以后惹别扭。常言说,亲不亲,财帛分。亲兄弟,还要明算账,何况是搁伙计?事先说好,以后不会因钱财反目成仇。”
我还想反对,张抓子也同意先分账,少数只好服从多数了:“那你们说吧,咋分都中。”
推让了一会儿,杜子京说:“你们都不想开河儿,我说一句吧,看中不中。咱们三个人三五、三五、三,就是你们两个说家儿每人各占三分半,我拉家儿占三分,咋样?”
“中,没意见。”我和老张都同意了。杜子京又提出一书一结,就是每说完一家的书,进行一次结算分账。我说:“那多麻烦、费事呀!一季度或一个月分一次账不行吗?”
杜子京说:“钱积累起来,让一个人掌握住不分账,既操心,也不安全,万一丢了咋办?不如收到一次钱就分一回账,各自操自己的心,保管自己的钱,花着也方便,一旦丢了,丢自己的不丢别人的,损失也小些。”
杜子京说得头头是道,满满的都是理,我无话可说,只得同意:“随你们的便吧”。唉,真是一个艄公一道河,同是说书行,规矩不一样。说书三四年了,和王老师、郭汉、王河清、刘大江、王遂厚、王矿子、王建平、李进银等说书艺人,搭过不同的班,却从没有经历过先分账后说书的事儿。王老师、郭汉,王河清老师都是非常地大度、厚道,总是在一个季度分手之时才开始分钱,分账比例上总是“争着不足,让着有余”,相互谦让。刘大江虽然小气,一分一毛的都看在眼里,但在搁伙计分钱方面却是一是一,二是二,非常仗义疏财。对杜子京他们这种先分账,“一把一叫唤”的做法说实话还真点不习惯,看不惯,看不起。虽然“先丑后俊”的理由富丽堂皇,但冷冰冰地缺少了人情味,丢失了最起码的义气和信任。入乡随乡,入俗问俗,和人家搭班,就得依人家的规矩,随波逐流,慢慢地学会适应吧。
次日,我们顺利地坐上了东去的火车。这帮“乌合之众”,东征巩县,到高手云集的河洛大鼓兴盛地去争食,会分得那么一杯粥吗?
[①] 数着:新安方言,数得着。
[②] 将:新安方言,激,激将。
[③] 脾气大:新安方言里,“脾气大”也作“大脾气”,指性格迟缓,行动拖拉,和“急性子”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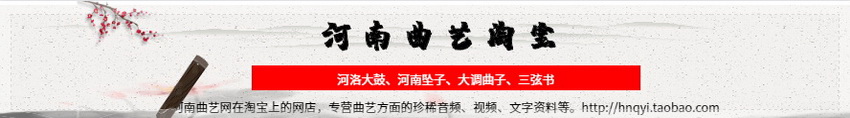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