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卅十

圪寮峪村位于站街去往大峪沟的途中。从站街出发,向东南方向沿沟逶迤前行大约三四里地,拐弯折向东北,进入一道不是太深的沟壑,一条不是太宽的土路高高低低,曲曲弯弯在沟底延伸。说是沟,但不是平的,感觉在沿沟往上走。路随沟左拐右折,忽上忽下,由于沟不是直来直去,总有岭头或其他障碍物阻挡视野,往前看不了太远,往后似乎又有土丘拦断了后路。领路的主家说快到家啦。我想,这地名真不错叫,这岭,这沟,这路,都是七扭八圪寮的,怪不得叫圪寮峪呢。
埋头走路很累,都闭着嘴不说话更加无聊。说说笑话,逗个趣,可以调节气氛,能有效地缓解疲劳。想起来刚才的话题,就没话找话,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毛捣老张:“张先儿,你弄这是球!给你娃子说媳妇哩,俺们被你拨得团团转,图啥哩?”
子京跟着附和:“就是。老张,今天你得请客,俺们都给你撺掇撺掇,要不然把这事儿捣腾黄。”
老张拍着胸脯保证:“放心,只要大家都搁把劲儿,努把力,想方设法把这桩婚事说合成,你俩都是大媒人,到时候不但领你们下馆子,吃酒席,每人还有谢媒的一块大肉。”
三人说笑着又拐了一个湾儿,眼前一亮,圪寮峪到了。
圪寮峪藏在北岭上的一个山洼里,四面环山,只有南边一条山沟曲折迂回地通向外面,成了唯一的出入口,外界很难找到。村子不大,百十户人家星星点点,参差不齐地分散在山谷两边。田禾、农舍相互映衬,两面岭上郁郁葱葱,或玉米、红薯,或桃树、苹果树,偶尔鸡鸣狗吠,炊烟袅袅,好一个世外桃源之景象。
进村不远,就到了请书的主家家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听说说书的来了,一面忙不迭地招待我们落座,安排做饭,一面跑前跑后地请人写神位,安顿神,挖香炉上香。这个愿书虽然不是太大,但总得摆上一桌供吧。得蒸供香糕,搁油锅炸果子,好多事呢。老太太忙不过来,就指使儿子:“去,把你二婶子、三大娘,你大娃嫂,还有二娃锈子叫来帮忙做供。”
“锈子”是啥?我一头雾水。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巩县的媳妇不叫媳妇,叫“锈子”。洛阳和巩县同属河洛流域,相距不远,口语很相近,说话都能听得懂,极个别词语说法不一样。如我们洛阳人的“袄”,和巩县的“袄”意思不一样。洛阳人的“布衫”,到了巩县人的嘴里,便成了“袄”。夏天穿的薄布衫叫“袄”,那冬天穿的厚棉衣该咋叫呢?人家叫“棉袄”。带里子的厚布衫,叫“夹袄”。反正巩县的口语里没有“布衫”这一说,分析一下人家叫“袄”也是挺有意思的。
和新安、灵宝相比,感觉巩县人更加热情好客,不怕陌生人,不欺外地人,待客之道是不分亲戚朋友,远近亲疏,一律以礼相待。招待我们说书人看不出任何的隔阂和歧视,亲如一家,让人倍感温馨。
巩县的饮食习惯和洛阳一带大致相同。新安县人厚道实诚,待客时用大黑圪篓[①]结结实实地捞上一碗古堆冒尖儿的面条,菜都没法浇,翻也没法翻,唯恐客人吃不饱。巩县人待客讲究,捞面条时用的是小花瓷碗儿,浅浅地大半碗儿,浇上菜刚好一碗儿,又好搅,又好翻。别担心碗儿小,不好意思回碗儿,吃不饱。人家早早地端上几碗儿放在桌上预备着哩,吃多吃少自己掌握,两碗不够吃三碗,吃不了一碗儿拨半碗儿,吃饱为止。
晚饭吃饱喝足,便拉开了书场。先是杜子京垫上一个书段儿,然后商量怎样开大书。考虑到我们的“特殊使命”,得让老张表现一下。我所会的大书《刘公案》《包公案》《彩楼记》《双锁柜》老张都不会说,只有让他拣自己拿手的大书来说。老张唯一的一部看家书是《双掉印》,也叫《回杯记》,又名《张廷秀私访苏州》。
头一次听张抓子说大书,说实话,嗓子不错。腔不大,音域不宽,却亮而净,很耐听。河洛大鼓传统的老腔老调儿,词儿也比较实,有些唱段儿很经典,我听一遍就留下很深的印象,如“王二姐思夫”一段,唱词很是精彩,把大家闺秀怀春、思夫、盼夫,相思入骨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如王小姐看张廷秀时,“小眼角里挂点情”;梦见相公,醒来时“热身子掉进冷水坑”等。老张唱这两句特别拿手,生动、细腻、传神,不止一次地唱,听得我也耳熟能详了。
老张的书没毛病,很是老道、熟练,无可挑剔,不慌不忙,四平八稳,但总觉得缺少点啥。个人认为,少了一种精气神。老张说书,不是太投入,没有把自己置身于书情里,与书中人同呼吸,共命运,而是成了局外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不入戏”。正因为自己首先徘徊在书外,不能融入书中,所以很难吸引人,把听众带进一种特定的情景中,给人造成一种说书“不带劲儿”“松不唧的”“凉” “听不热”的感觉。怪不道新孟两县,不管是说书的,还是听书的都调侃:名叫张抓子,书却“不抓人(吸引不住听众)”。
果不其然,一板书下来,听众不温不火的,反应冷淡,书并没有“入馈”[②]。老张脸色有点灰土土地尴尬,杜子京屁股在椅子上拧来拧去,很是焦急的样子。这时主家发话啦:“老师傅累啦,好好歇歇,换人说吧。”
大本头书千头万绪,开头部分交待故事,展开情节,往往会有过多的铺垫,故大书的开头部分大多都有点“凉”,不热闹。老张自知第一板书没说住,害怕听众跑路,所以没敢大歇,稍微喝口茶,喘了一口气儿,就重新掂起了鼓板,刚要开始,听到主家说要换人,只好又无趣地把板放下,将求助的目光投向我:“吕先儿,那你来吧。”
我摇摇头:“来不了啊,这本书我又不会,接不上,咋说呢?”
杜子京急得在一边儿插话:“吕先儿,赶紧救场吧。《双掉印》能接得上就接,实在接不上,只好另开大书了。”
有人疑惑,你们这说书的,在书场里对着那么多的听众,就这样商量来,商量去的,就不怕煮烂的饺子——露馅了,让别人笑话?众位有所不知,我们说的不是普通话,而是江湖说书行中的言之话,也叫“春点儿”,是一种黑话,行话叫“暗纲”,行外人是听不懂的。用正常话说出来的叫“明纲”,有些话不想让听众听到的,就要 “递暗纲”。
主家拿眼睛看着我,老张把说大书的任务往我身上推,杜子京在一个劲儿地摧,我心里七上八下地没了主意:接《双掉印》吧,老张说的这部书一遍也没听过,不是我的菜,不擅长,怕弄砸了;换大书吧,已经说过一板了,中途换书如临阵换将,是说书行之大忌。重打鼓,另开章,弄不好,换书会把听众换跑得更快。唉,好不难煞人也。
这么多人盯着,那么多听众等着,来不及过多的迟疑和思索,脑子急速转了二十四圈儿半,啥,咋还有半圈儿?瞎,最后这一圈儿转到一半儿,一拍脑门儿,把主意拍出来了:还接着《双掉印》说!
《双掉印》虽然没听老张说过,但并不是完全不熟悉,早有耳闻。学生时代,不止一次地听说书人唱:“想听文的《包公案》,想听武的《杨家兵》,半文半武《双掉印》,苦辣酸甜唱《红灯》……”那时候就知道有《双掉印》这部书了。所幸的是去年春和宜阳的王建平搭班在黄河北说书时,王建平的拿手书也是《回杯记》,就是老张的这个《双掉印》。我听过两遍,大致情节记了个差不多,并时不时地接上几板。虽然对这本书并不是太感兴趣,并没有打算下劲学精,但偶尔抵挡一下还是没有问题的。感谢王建平让我接触了这部大书,又感谢刘大江教会了随机应变、触景生情,“胡球弄”的能力,到关键时候,又派上用场了。
于是,拿定主意,毅然登场,鼓响弦起,接着王月英的“哭楼”徐徐道来。听过《张廷秀私访苏州》的都知道,“王月英哭楼”是细书,是整部书的精华,能否吃得开,叫得响,凭的就是这一段儿。老实说,这段词儿我并没有掌握住,远没有人家老张的词儿实、准确、经典。只好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硬着头皮,滥竽充数,东拼西凑地来组织“哭楼”的词儿。情急之中,把《双锁柜》中余蒲姐哭楼的词儿换了个人物,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狼拉狗扯地“强加”到王月英的头上,生造了另一个版本的“王月英哭楼”,好歹总算是糊弄过去了。
限于咱的水平,这一板书谈不上说得有多成功,感觉原书中好多的精华都没能很好地展现,好多细节的书味也未能演绎到位。只是凭自己年轻,有劲儿,卖力,敢冲敢闯罢了。但听众好像听进去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休息的间隙,下面有人提议:“让秋花说一段儿”。
一听说“秋花”这个名字,老张立即像打了鸡血一样提起了精神,两眼放光。原来这个叫秋花的就是老张提到的那个跟他家孩子张建营谈过的姑娘。
老张介绍过,秋花姓尹,两年前拜师站街水峪沟著名的老艺人廉保乾学唱河洛大鼓,廉保乾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不能出门,就又跟着他的儿子廉玉民学艺。后来,因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原因,不跟廉玉民厮跟了,待在家中。
尽管尹秋花尚未完全学艺到家,不会拉弦,目前仅说几个书段,不会大书,但对于我们西路艺人来说,仍然倍感新鲜,羡慕不已,觉得人家真了不起。因为新安孟津两县女孩子学说书的极为珍稀,偶尔有女性习学的,除新安县的侯秀英学艺有成外,大多都半途而废。
所以,不仅老张为之一振,我和子京也不由自主地提起了兴趣,一齐往书场下面望去,有几个妇女有推有拉,有说有笑地劝一个女子:“上去呗,一个村的,说一段儿让大家听听。”
靠后面灯光照不到的阴影里,我们看不太清面容。只见秋花一边往后躲,一边儿推辞:“经常不说(书),已经说不成了。”
老张不失时机地邀请:“来呗,既然都说出来啦,就说一段吧,把大家的面子拾起来。”
秋花在暗处冲我们摆摆手:“不耽误事儿,你们说(书)吧,不要听他们的。”
可能姑娘家矜持、怕羞的天性使然吧,任凭众人怎样起哄,我们怎样诚邀,尹秋花终究躲在后边不肯露面儿。初次见面,我们也不好强求,但第二天中午说神书时,尹秋花竟然提前到场,大大方方地与我们见面,并主动地招呼和问候。
昨晚在灯影里未及看清,今日她亭亭玉立,落落大方地一站,让神案后的观音像黯然无光,让其他人逊色,让我们自惭形秽。装作不经意地瞟了一眼,为啥不经意,为啥只瞟一眼?倒是想正儿八经地,好好地,正面多看几眼,不敢哈。你想,刚见面不熟悉,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人家姑娘家死看,多不礼貌,算啥人哩。所以就假装往别处瞅,有意无意地顺便扫了一眼,不由为之惊艳!
她二十岁上下,和我年龄相仿,云盘大脸,杏眼蚕眉,披一头当下时兴的“大波浪”,更显得风姿绰约,气质非凡。一双会说话的,水汪汪的大眼惊鸿一瞥,让人走神,发神经,目瞪口呆。
失神之余,不禁心中拿尹秋花和张建营做了一个比对和权衡。老张的儿子张建营我见过一面,长得有五短,却没有三粗。身材短、胳膊短、腿短、脚短、手短,腰不粗、胳膊不粗、腿不粗,有些蚂蜂细腰的样子,要个子没个子,要气力没气力,要能力没能力,和尹秋花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没有可比性。很难想象,这小子凭什么本事,什么妙招,能和如此漂亮的说书女子扯到了一起,不服气不中啊。
不由得暗暗嫉妒起张建营来,他娘的这家伙艳福不浅啊!忿忿不平地想,为什么好白菜都叫猪拱了,为什么鲜花偏插在了牛粪上?再一想,感到自己好笑,八字还没一撇,猪能不能拱住白菜,牛粪能不能养住鲜花,倒还不一定呢,嫉的哪门子妒?想到此,顿觉释然,心理平衡起来。
话又说回来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既是搁伙计,岂可生二心?成人之美是传统美德,不可辜负老张的一片苦心啊。再说有俗言:好汉没好妻,赖汉还能娶个花滴滴哩。猪八戒还能钩上月里仙女嫦娥呢,谁说张建营就不能娶个漂亮媳妇?一切都有可能,万事皆有定数。不但不能嫉妒,还得默默祝福。愿老张不虚此行,好梦成真;愿张建营尹秋花好事多磨,终成眷属吧。
对尹秋花的到来,最惊喜得手足无措的莫过于老张了。?得忙不迭地站起身来迎接,点头哈腰地让座,极尽献殷勤之能事儿,唯恐有失礼得罪之处,惹人家不高兴。我也尽量做出潇洒的样子,彬彬有礼地邀请:“初次见面,唱一段让俺们欣赏欣赏吧。”
杜子京不失时机直呼其名地恭维:“秋花,早就听说你的名字啦,书说得老好听呀。今儿咋着也得赏脸儿,唱一段,叫俺们见识见识。”一边说着,一边忙不迭地掏弦子。谁说子京脾气大,做事慢?那得分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你看这会他比任何人都利索,麻利的掂起了弦子,三两下就定好了弦儿,净等着秋花开唱。
说话不及,老张把鼓板也准备停当。秋花也不再推辞,大大方方地接过钢板,忘不了说一些自谦的话:“俺才学的,唱得不好,让老师们见笑了,多多指点。”
秋花唱了一个书帽《猛虎学艺》。女声就是柔和、纯净、圆润,听起来入耳、甜美,加之姣好的形象、气质,很是让人陶醉。尽管唱腔不是太老练,尚欠火候,略显稚嫩。与其说是说书,倒不如说是背书,感情、语气不是太到位,没有把书说活。但一俊遮百丑,何况人美、腔好不止一俊?足以鹤立鸡群,让我们相形见绌了。一曲下来,大家纷纷叫好。
关于秋花和张建营的事儿,预先我们同老张商量过,认为这件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可能适得其反,得慢慢来,不能刚见面就提婚事,一旦说嘣了,搞砸了,就不好收拾啦。老张也是有心眼,讲究方式的人,有关建营的事儿绝口不提,趁着大家的高兴劲儿,试探着问道:“闺女,在家没事儿,跟着俺们搭班出去说书吧?”
秋花犹豫了一下,笑笑:“俺也学不成景,可长时间没说书,不想出去了,再说爹妈也不叫俺一个姑娘家疯疯颠颠地跑,让人笑话。”
杜子京抢着说:“可不敢啊,(说书)已经学到这种程度,丢功了多可惜呀!跟你父母好好说说,出去吧。再说巩县女子说书的多得是,又不是你一个,人家都不怕笑话?新社会啦,不能老封建。”
秋花说:“巩县女说家是很多,像牛会玲、李新芬、黄金焕、韩淑玲……,可人家都学有所成,已经出名了。俺不带那苔儿,说得不好,出去了连累你们跟着丢人。”
子京天生的有厚着脸皮套近乎的一套本事:“秋花,你说的书俺们非常看好。相逢就是缘,觉得你这人说话老好,咱们老对脾气呀,说啥也得合作一回,要不然俺们走后心里会一直不得劲儿,落下遗憾。”
“老好”“老对脾气”这类俗不可耐的肉麻话只有杜子京能说得出口,换换我打死也说不出来。此言一出,秋花的脸有点红红地不好意思,一时支支吾吾地不好回答。
见大家一致相劝,要不说话,弄得我倒像哑巴似的,等了半天,终于有了插话的机会,也就不甘落后地说:“咋?嫌水平低,跟你搭配不上,不想跟我们厮跟,害怕丢你的人?”
秋花连忙笑着辩解:“说到哪去啦。不是你们搭配不上我,是我搭配不上你们好不好!俺是害怕书说得不好,出去拖老师们的后腿。”
我说:“只要不嫌弃俺们,谁搭配不上谁还不一定呢,说不定俺们还能跟着你沾光哩。不用找恁些理由啦,再推来推去的,就是看不起人啦。”
话说到这份上,秋花沉吟了一下,说:“好吧,我回去跟俺爹俺娘好好商量一下。”
终于松口了,有门儿!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好,等你回话。”
次日又见面时,尹秋花带来了好消息:回家软磨硬泡,软说硬办,硬是做通了工作,说服了父母兄嫂,同意她和我们一起出去说书了。老张止不住喜形于色,按捺不住激动高兴的心情。来巩县、到站街,至圪寮峪,见尹秋花,答应出去说书,一切按他原计划进行,顺风顺水的,没有一丝磕拌。只要在一块搭班,事儿就成了一半,岂能不狂喜,偷着乐?
和尹秋花在一块说书,当然也是我和杜子京巴不得的。抛开替老张办事儿,替建营说媳妇的公开幌子不说,背后也是有些见不得人,说不出口,摆不到桌面上的一点小私心的。常言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更何况是年轻貌美,志同道合的一行人?说书几年来,和老师,和朋友,交的同行,搭的班口也不少,但都是清一色的“和尚班儿”,“光杆儿队”,和女性说书的在一块儿合作,一定充满生机、活力和情趣,让人神往和期待。你别笑俺成色低,见漂亮女子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同性相排斥,异性相吸引,是自然规律,是人的天性,我等凡夫俗子,岂可避免?
就在我们为自己取得第一步的胜利成果而洋洋自得,沾沾自喜时,另一件棘手的事儿又开始困扰了。除了灵宝说书时兴七八个人的大班口外,河洛大鼓在乡村演出时都是小打小闹小班口。无论河洛流域,还是黄河北,说书一般都是二至三人一班,巩县亦然。三人已经是大班口,现在添了一个尹秋花,变成了四个人,超限了。多出一个人,就多出一份开销,书价得相应提高。请书的不但多花钱,还得多管吃住,陡增了负担。我们说书的虽然轻松了,热闹了,掏钱请说书的却吃不消了,不想干了。请说书的人少了,生意就不好了,钱就不好挣了,大家也就高兴不起来了,弄到最后还是要散伙了。
私下里我把自己的担忧向老张和子京说了,他们也感到确实是个问题,人多钱多花费大,势必会影响说书生意,场次不稳定,日子也不好过。怎么办?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犹豫再三,我下了决心,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我们分班吧。”我说。
老张和子京几乎惊疑得异口同声:“分班?咋分?”
“是这样吧,咱们四人分成两班儿。老张,你的儿子建营不是在巩县吗,他的手里不是也有证明吗。别忘了来这里的目的和正事儿,你把证明留给我们,领着尹秋花找到建营,你们三个人搭班,不是正好给他们在一块儿创造机会吗。只要能搅合到一块儿,你再趁机推波助澜地撮合一把,事儿不就成啦!我和子京趁你的证明还能凑合一班儿,这样两不耽误,看这中不中。”
老张听了这一番话,几乎是感激涕零,要不是比我年长得多,恨不得下跪表示感谢,连连拱手,冲着年龄和他儿子差不多的我称兄道弟:“哎呀,老弟,你可真是实心实意地替哥着想,替哥办事啊!放心,这事儿成了,你就是你哥和你侄儿的大恩人,一辈子都会记着兄弟的好处。”
杜子京听了却不以为然,持不同意见,等老张说完,才迟迟疑疑,慢吞吞地说:“你们光想得怪美,人家秋花愿不愿意?巩县的书好说?巩县的说书饭碗好端?巩县的说书行好混?本来咱一班儿的力量还可以,勉强能站住脚,这一分开,拆得五零四散,势单力孤,谁也干不好。老张,凭你和建营的书在巩县能站住脚不能?要是自己顾不了自己,秋花会死心塌地跟你家建营吗?”
杜子京一席话噎得老张无言以对。其实杜子京是什么品行,打的什么小九九儿,我心如明镜,一清二楚。他不想轻易放弃好不容易得到的能和秋花在一起的机会,因此才想方设法,以各种理由,各种借口来百般阻挠分班。杜子京之心,路人皆不知,我却知也。
坦白地说,杜子京的想法何尝不是我所欲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不想体验一下男女搭配说书的新鲜感,刺激感?刚相识就分开,心里总有一些隐隐的不舍和不是滋味。但答应替人家老张办事,一诺值千金,就应该抛却私心杂念,尽心尽力,责无旁贷去兑现。心中无私天地宽,除去杂念路途畅。
子京说得也不无道理,我无意揭底和反驳,就打圆场:“这是咱们在一边儿商量哩,分还是不分,怎样分,明天征求一下尹秋花的意见吧。”
三天书结束,该启程了,老张向尹秋花表述了想分为两班的意思。尹秋花还没听完,就坚决地反对,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不能分班,不能为了我把你们的班口拆散。要搭班就是咱们四个人在一起,谁也不能离开。要不然就当没说,我还在家。”
我耐心地解释:“俺们也想着四个人在一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多好,不想分开啊。可是四个人班口太大,担心活不好找啊。不要紧,既然认识了,一回生,二回熟,往后有的是合作机会。”
尹秋花很干脆地说:“不是担心人多,钱多,书场不好联系嘛。咱丑话说在前头,我是跟老师们一块出去玩的,一分钱的工资也不要,四个人还按三个人的书价,这总可以吧?至于多出来一个人的吃住,你们不用操心,我有办法。要不这样还不行,你们该走就走吧,我不出去了。”
话说到这份上,我们也不好意思再坚持分班了。老张说:“闺女,话是这样说,哪能不要工资,账该咋分咋分。放心,逮一个蚂蚱,也要分给你一条腿的。任凭俺们少要点儿,都不会亏了你。”
我挥挥手:“啥也别说啦,咱们四人同舟共济,有苦同吃,有难同当,有福同享,齐心协力,把书说好。”
[①] 圪篓:新安县大山以下烧制的粗瓷大碗,俗称“圪篓”,因釉子是黑色的,也称“大圪篓”“大黑圪篓”。
[②] 入馈:江湖说书行话,听众听书,听进去了称为“入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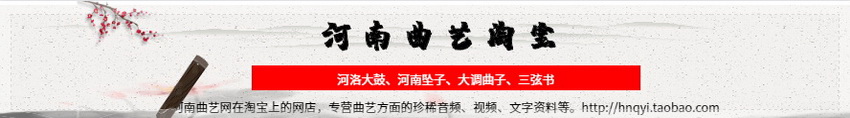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